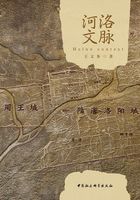
第四节 《洛阳伽蓝记》的文学经典价值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名寺的兴废沿革,由城内而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以极富条理的空间顺序,依次记载每一座伽蓝的兴衰始末。以记佛寺为题,融入历史事迹、风俗习惯及种种传闻典故、灵异故事等。从宣武帝以后的皇室变动,到宗藩废立、权臣专横、宦官恣肆、艺文古迹,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俗等,无不详记,使一部地理类、历史类书籍,充满文学的趣味,又可以补充《魏书》《北史》之不足。《洛阳伽蓝记》符合小说演进的各种特质,题材由志人志怪演变为兼融史传笔记、稗官野史与神怪杂录、民风异俗,超越六朝小说题材;艺术手法由先前的缺乏结构主题,到结构曲折,主题繁复;文字由单纯叙述到有叙述有描写,间杂俗语和对话;文采由朴质记录到骈散并行,修饰烘托,成为介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每一则独立为小说来看,以清丽典雅的文字记述史传、古迹、艺文、风俗、灵异等故事,素材类型、艺术成就以及对洛阳文人史料的记载,可谓中国文学史上一块丰碑。
一 题材特征
记述洛阳城内奇人异事。六朝清谈放达,品评人物的风气大盛,这种风气已影响及小说。《洛阳伽蓝记》中有许多丰富的记人文字,写人性情,鲜活生动。如第2卷“龙华寺”[10]写寿阳公主一段故事:
明帝拜综太尉公,封丹阳王。永安年中,尚庄帝姊寿阳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授齐州刺史,加开府。及京师倾覆,综弃州北走。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宁受剑而死,不为逆胡所污。”世隆怒之,遂缢杀之。
这段故事没有直接描述公主性情,却用对话表现公主极为贞洁刚烈,笔法形神兼备。
“高阳王寺”[11]载:
(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辩,神情卓异,虽黄琬、文举,无以加之。正光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子文摄齐北面,就和受道。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子文对曰:“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才无以对之。崇和曰:“汝颍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信非虚言。”举学皆笑焉。
这段文字颇类《世说新语》,先叙人物,辅以故事,来证明荀子文聪辩。除了真实的人物外,也写虚构的传闻,譬如“建阳里”[12]中的赵逸: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汝南王闻而异之,拜为义父。因而问:“何所服饵,以致长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尝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记旧迹,三年以后遁去,莫知所在。
杨衒之极力把赵逸描写成一位隐逸高人,能洞察世事,智慧高超,并时时让他出现在书中,作为各种事件的见证人。这段文字记载赵逸,文末以汝南王问赵逸答,来刻画赵逸的神奇性格。
《洛阳伽蓝记》记述人物,无论官场中人或市井小民,也不管是文士贵族、异人高士,或雅人、小人,均如《世说》 《人物志》一样生动形象,充满情趣。如“法云寺”[13]记元彧一段:
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风仪详审,容止可观。至三元肇庆,万国齐珍,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疲,莫不叹服。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采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郄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荆州秀才张裴裳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彧以蛟龙锦赐之,亦有得绯绯绫者。唯河东裴子明为诗不工,罚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时人譬之山涛。及尔朱兆入京师,彧为乱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这段文字写元彧性情风流如仙,颇有《世说》旨趣。还写人物聚会,赋诗相赏,从中可见当时洛阳文人习尚。
《洛阳伽蓝记》保存了大量的神怪故事,为后代《太平广记》等书主要的辑录来源。譬如“昭仪尼寺”[14]一条,即存有两则异闻:
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中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暝,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段晖宅)地下常闻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时人咸云“此荀助旧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陨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
此外,还有“法云寺”之狐魅故事,“白马寺”经函时放光明,“宣忠寺”元徽投寇祖仁家遇害的冤报,“平等寺”佛汗故事,等等。或长或短,叙述精简,骇人听闻。有叙述,有对话,笔法变化在六朝志怪小说上。记述有因果、灵验、报应、神狐等素材,兼有宣讲神怪和说明因果报应的双重趣味。
记述历史,并有史家评说。杨衒之笔下的历史,有些是见于史籍的信史,有些记述可弥补史籍不足;有些是演义,渲染强化民族意识。志史文字不仅具文学趣味,也富有史识史评。譬如《魏书》卷11载:“正光二年,正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帝以元义擅权,遂称疾不起。久之,因托音病。”同样一段历史,杨衒之在“平等寺”[15]记云:“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义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永安中,巡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执而送之。庄帝疑恭奸诈,夜遣人盗掠衣物,复拔刀剑欲煞之。恭张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庄帝信其真患,放令归第。”
杨衒之这段描写比《魏书》更具体生动。此外杨衒之在志史的过程中加以史家评论。如“永宁寺”记永安三年尔朱兆囚庄帝于寺,交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宜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境,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16]揭露尔朱氏祸国丑态,义正词严,文字笔法介于史传与小说之间。
记载很多魏人迁居洛阳时的民风异俗。反映当时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也是丰富的小说题材,如“法云寺”[17]诸王竞奢:
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
同一段记载中也描写元融竞奢,最后以“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积于廊者,不可较数”结语。时俗之弊,令人骇异。此外,也记载了各种宗教习俗、外来传闻和南北生活异俗。[18]
思想内容上,有对时政和陋习的讽刺,有对南北正统的辨正和佛教义理的反省,比起纯粹的记述更接近小说笔法。杨衒之不信仰佛教,并且不赞成佛教的畸形繁荣,因此他的伽蓝记,没有陷入宗教情绪,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具有信史史料的价值。
二 卓越的小说艺术
首先叙事结构上,《洛阳伽蓝记》序言介绍本书体例:“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五篇。”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共5卷。每卷以若干个寺院为单元,如城内分别记载永宁寺、建中寺、长秋寺、瑶光寺、景乐寺、昭仪尼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轻重主次,条理清楚。各卷各寺之间又血脉相通,例如当时弘扬佛教,大建寺庙最有力的宣武帝皇后胡氏,即灵太后,在书中反复出现。陈留侯李崇在几则故事中都有记述。第2卷城东“正始寺”[19]:“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第3卷城南“高阳王寺”[20]:
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亦常无肉,只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佑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裕曰:“二九(韭)一十八。”闻者大笑,世人即以为讥骂。
第4卷城西“法云寺”条下“开善寺”[21]: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
李崇贪财吝啬,而又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大施主形象,跃然纸上。
同样一个人物在各卷中出现,互相呼应;同一事件散见各卷,互为补充。结构回旋中,隐现寺庙铺张浪费,将引发道德危机和政治动乱的线索。
开创正文和子注互相映照的叙事模式。《洛阳伽蓝记》正文外,又有一些自注。虽然这种办法历代学者多不认可,但在中古时代颇为流行,也自有其妙处。正文与子注视角不同,取材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读起来更有兴味。如卷一城内“永宁寺”,是本书记述的第一个寺院,叙述篇幅最长,子注也最多,大概因为永宁寺来头极大,建筑最为富丽堂皇,是洛阳的一大地标,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也最多,正文开头: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临御史台。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甕(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者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登。[22]
所谓“刹”乃是塔上之塔,印度、尼泊尔的塔原是一个实心建筑,可安放佛骨和其他遗物,而中国式的佛塔是空心可登临。塔上加宝瓶和承露金盘,与中国传统信仰结合,所以要细加说明。正文加注,介绍永宁寺地理位置的同时,更详细说明这一带的重要建筑物;在“常景为寺碑文”句子下面,又详细介绍常景其人;在“禁人不听登”下又添一短注:衒之曾经与河南尹胡孝世一起登上过这个塔。用亲身经历来印证前文的叙述。这样空前雄伟豪壮的庙宇和宝塔,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技术,也洋溢着当时皇室狂热的宗教情绪。可是就在这庄严神圣的庙里,却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正文继续写道:“至孝昌二年(526)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建义元,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
十多年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北魏王朝由此走向了衰败和分裂。作者于此段正文几乎一句一注,介绍了大量的相关史实,特别是关于尔朱荣入洛,诛杀王公卿士及诸朝臣二千余人,以及由尔朱荣扶上台的魏庄帝元子攸用非常手段诛杀太原王尔朱荣的经过,叙述非常清晰,中间又夹了一段元子攸从兄元颢自行上台称帝的插曲,把北魏王朝变故迭起、国将不国的乱局作了很好的交代。凡此种种,皆足以与《魏书》互证,其中的许多细节且为史书所不载。如果不加子注,这些珍贵的细节材料就将遗失不存,记述也少了许多兴味。
骈散结合,夹叙夹议。《洛阳伽蓝记》叙述用散句,写景时多用骈句,笔法灵活从容,于随意中见情志,毫不装腔作势或哗众取宠。如第1卷“景林寺”[23]:
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寺,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有石铭一所,博士卢白头为其文。
第4卷城西“宝光寺”[24]:
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四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堂。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堂下犹有石数十枚。当时园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叹息焉。园中有一海,号曰咸池,葭菼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普泰末,雍州刺史陇西王尔朱天光总士马于此寺,寺门无何都崩,天光见而恶之。其年天光战败,斩于东市也。
三 保存了很多关于洛阳的文学史料
《洛阳伽蓝记》引用了很多洛阳地方的民间传说、故事和谚语,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元素。无论是正文还是注文,在合适的地方杨衒之很喜欢引进民间文学,让行文充满生气活力。如第2卷城东“崇真寺”[25]一上来就说“比丘慧嶷,死一七日复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下面大段记录慧嶷的回忆,归结为比丘应当禅诵,不必讲经。这些民间传说反映了当时佛教的风习变化。第3卷城南“大统寺”[26]附双女寺文后有一较长子注:
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馐,海陆具备。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渌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这则神奇故事记述洛水之神服役,而其家族以溺死孩子的鲜血为酒款待他的同僚。想象诡异,为后世民间故事借鉴虚构的素材。
《洛阳伽蓝记》多处引用谣谚,如第1卷城内“瑶光寺”,记述寺中有很多漂亮尼姑,于是引用“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来说明此寺。第4卷城西“白马寺”中,说白马寺盛产高级水果,于是就引用谚语“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第3卷城南归正寺中,说到伊洛河里的鱼,于是引用谚语“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等等,给行文平添很多趣味。
介绍了当时洛阳文人逸事。第3卷城南“报德寺”条下写到洛阳城南延贤里内“正觉寺”[27],介绍兴建正觉寺的王肃,因家难由萧齐投奔北魏的故事,其中详细记述了王肃前后两位夫人写诗赠答:
肃字恭懿,琅玡人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494)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王肃两任妻子出身都很高贵,前妻谢氏出身于江南世族,其父谢庄是著名的文学家;第二任妻子是北魏孝文帝的妹妹陈留长公主。王肃本来在南齐当官,因为父亲王奂被萧齐武帝诛杀,不得已投奔北魏。此时正值孝文帝大力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王肃凭他的才能得到赏识和重用,又被北魏王室招为女婿。谢氏追到了北方,于是王肃就成了两位夫人争夺的对象,处境十分狼狈。王肃建一座庙来安置谢氏,乃是不得已的举措,但就诸如此类的尴尬情况来看,这个办法后来还相当通行。谢氏的五言诗里包含着很深的哀怨和讽刺,她说你王肃像一条蚕,原来在箔上养着,后来爬上去了,你还能多少记得些原先的事情吗?这里的“丝”“路”“胜”都有谐音双关的意味,大有南朝民歌的风味。情幽语细,胜于明写哀怨,这正是运用比兴手法的妙处。公主的答诗则充分肯定了喜新厌旧的正确性,坚持现在的婚姻状态不容改变。但当时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不久,尚存蛮风,公主能用比兴手法写诗以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已经非常风雅了。王肃虽然文化修养很高、极有文采,但绝不能开口,当务之急是把谢氏安顿下来。
记录文人作品、文坛逸事和文学相关的社会风气等。从书中可知,当时文人游览或集会时,与南朝相似,习惯于作五言诗。例如第5卷城北“凝玄寺”[28]条描述该寺:“地形高显,下临城阙,房庑精丽,竹柏成林,实是净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可见洛阳当年诗风之盛。[29]
总之,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城市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把洛阳城作为描述对象,是城市文学审美的经典;充分描绘了北魏时期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情景,展现了城市、文学与文化等多维度的融合演进,在整体上呈现出北魏都城洛阳的生存状态和风土人情。把洛阳城市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洛阳伽蓝记》构建了城市文学的审美类型,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品格。[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