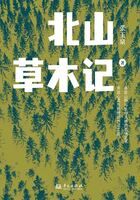
第20章 草木的味道
听说李时珍所到之处,皆品尝百草之味。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我是从小翻过若干遍的。医书并未标注草木所治之病,也大概从未标注其气味和味道。而我认真品阅书中的草叶样本,也大概喜欢它们的本性罢。
其实,田野就在门外。抬脚出门,就可见野草遍地。别说村外,村子旮旮旯旯,都布满了数不清的野草。
我对草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小时候粮食并不宽裕,山谷贫瘠,人多地少。饿肚子是村子上穷人家孩子常有的事。我小时候,饥饿难耐,就常常往山野里跑。徜徉在山野荒草间,自然对山间各色草木的味道了若指掌。
走在河边或者山路上,单凭那些光线的明暗和草间传来的气息,就能辨别出此处生长着何等的植物。传说何首乌是一种神奇的植物,吃了是能成仙的。何首乌虽是北山上一种常见的植物,据说却能在不经意间发生游移。这种现象我并未亲身经历,却常常听奶奶提及。一些事情本无定论,传说与现实交杂呼应,只是成为一种介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映照和参考。
何首乌为何生成为人的形状,而且又分雌雄,没有人研究,也没有人发现其中的奥秘。而何首乌特有的气味,那种微苦而又恒毅的味觉,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嗅觉器官里。倘若走过山间小道,抬头看一看山间的光线和明暗,大概就会猜得出必定有一株何首乌藏在那里。
再者,还有河道里的水芹。水芹的味道十分特别,清淡的香味带着特有的辛腥,群居在水边。水芹在水边繁衍,我就在水边采摘。一篮子一篮子地采回家里,母亲用热水烫了,便成了可口的菜肴。水芹从来不会因为河道的狭窄和河水的减少而消失,相反,它们在春天到来的时刻,从河岸上蜂拥而出,在杂草间繁茂成长。只是,它们已经被定义为荒草,再也没有人去邀请它们坐客村人的饭桌。去年回家处理三哥的后事,路过故乡东河,姐姐看到水芹菜就挪不动脚了。她跟大嫂两个人蹲在河边,采了一大把上来,非要我返京时带上。看她俩浸湿了鞋面和满是汗水的脸孔,虽然心动但还是于心不忍。再说夺人所爱也不是我的性格,于是坚持不带。可等我登上高铁,翻看背包时,却发现水芹早已淘洗干净捆码齐整,安静地躺在我的背包里面。
记忆中的白头翁是故乡山上常见的植物。因其花朵酷似瓷碗碎片的形状,村里人都称之为打碗花。有一次,我去山上看到淡蓝色的打碗花绽放花朵,喜欢得不行。于是采了一束,拿回家放在厨房的窗户沿上,被奶奶发现后扔出来了。去问理由时,才知道村里人都传说打碗花放在厨房,会引起碎碗。当时惊惧得很,再也没敢去采打碗花。现在想想,大概是那时生活贫穷,碗都极其珍贵,有的碗可能会用几代人,所以大家才有这样的忌讳。至于白头翁为何冠以此名,我当时大概猜测是它开花之后,满是白须,酷似老者的白发而得名。
白头翁真正的传说与诗人杜甫有关。传说杜甫困守京华之际,生活异常艰辛,因吃了剩饭而呕吐腹泻,无钱医治。恰逢一白发老翁路过,采来一把满是白色柔毛的野草,让其煎汤服下,得以痊愈。因此就将此草起名为“白头翁”,并写下了“自怜白头无人问,怜人乃为白头翁”的诗句,以表达对那位白发老翁的感激之情。当时白头翁确实作为村头药铺每年必收的药材。每年寒假,父亲总要带着我去刨白头翁根,完成学校勤工俭学任务之外,多余的晒干卖到药铺里去。
除了白头翁,血参根是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野生药草。这种植物一般生长在贫瘠的山腰,或者夹生在石头缝里。因药铺购价昂贵,一度从两毛钱一斤涨价到五毛钱一斤,父亲于是常常备了干粮带我去南山采摘,运气好的话,一天能采上二十来斤。在我印象中,血参叶片类似薄荷的叶子,味道刺鼻,开蓝色如槐花状的花朵。血参根系庞大粗壮,根表血红,直觉应该是与补血有关。实际上,它的学名是丹参,有活血祛瘀、凉血消痈、除烦安神疗效。父亲后来还运用经济头脑,把刨来的新鲜血参根栽种在河边菜园子里,但印象中收成并不太好,后来大概放弃了。
还有北山的兰花。兰花在农村并无人关注。只是姐姐喜欢兰花,她喜欢唱《兰花草》。“你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歌声清纯淡雅,带着些许感伤,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有一次,兄弟姐妹们一起到北山上游玩,回来采了一株兰花栽进脱了底的洗脸盆里。兰花一直波澜不惊,安然若素地生长在屋檐下,有几次还被家中的老公鸡啄断了枝叶。这株兰草在寂寞的院落里陪伴我走过了小学的五个年头,最后竟然开出了淡黄的花朵。而我也从此喜欢上了兰花的从容与高洁,时常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边读书,一边品赏几线兰花丛叶的疏条,内心竟也有了几分诗意。
兰花却也有仙意的,至少在我的内心,它的性格里面仿佛藏着无尽的姻缘与神秘。每当我踏上北山,走在山间的某个地方,就能觉察到兰草的存在,不用寻找,一株株兰草就会在某个时刻准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多年后,我带着孩子回家,到村外去感受山野的风情。不料在我童年时曾经发现兰草的地方,蓦然发现依然有几株兰草等待在那里。多年的情感在瞬间从内心发酵,让我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