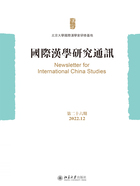
漢化佛教東傳日本中的“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史意義—從敦煌到奈良
張曉明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
漢化佛教東傳日本既是文明超越地理邊界傳播的標誌,更是中國文化傳播意義下知識流動的重要體現,它對日本本土佛教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回顧漢化佛教的東傳,它的傳播軌迹不僅跨越了地理空間,還顯示出文化(culture)越境的内層意義。目前,中日學界對於佛教在日本的傳播研究,主要聚焦在包攝佛像、佛經的文獻、藝術、宗教、哲學的傳播 1,其中也有不少學者論及敦煌佛教與日本佛教的關聯性 2,特别是敦煌寫經與聖德太子的《三經義疏》之間的聯繫 3,却鮮有研究將漢化佛教作爲文化意象審視其東傳日本過程中的傳播史意義。因此,本文將漢化佛教的傳播看作文化意象,在爬梳佛像與佛經等在日本飛鳥時代傳播的基礎上,通過探討聖德太子《三經義疏》的真僞問題挖掘其内裏隱含的“絲綢之路”的傳播意藴,進而超越從敦煌到奈良的地理空間意識分析漢化佛教東傳日本中的“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史意義。
一、佛像與佛經在飛鳥時代的傳播
關於漢化佛教傳入日本的記載,在《元興寺緣起》“佛本傳來記”有“天國押排廣庭天皇(欽明天皇)磯嶋宫御宇卅二歲之中第三年壬申,百濟明王,佛像經教奉度日本”的記載 4。而《元興寺伽藍緣起》又記:“大倭國佛法,創自斯歸嶋宫治天下天國案春岐廣庭天皇御世,蘇我大臣稻目宿禰仕奉時,治天下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度來,百濟國聖明王時。太子像並灌佛之器一具及説佛起書卷一篋度而言,當聞佛法既是世間無上之法,其國亦應修行也。”5據此可知,代表佛教的佛像、佛經應是經由朝鮮半島的百濟在欽明天皇即位的前一年(538)傳入日本。但《日本書紀》所記略有不同,“(十三年)冬十月,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6。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百濟聖明王時,釋迦佛像、幡蓋以及佛教經卷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552)。雖然《元興寺伽藍緣起》與《日本書紀》的記載時間略有齟齬之處,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認爲佛教是在6世紀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經由朝鮮半島傳入飛鳥時代的日本。因此,佛教也是飛鳥文化的主要代表。
然而,對於飛鳥朝的日本而言,佛教的傳入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深奥、複雜的佛理有了充分的理解,當時的人們主要還是把佛教當作一種咒術來祈求福報。於是,來自中國、朝鮮半島的佛造像對飛鳥朝的社會信仰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佛像也成爲飛鳥文化極具代表性的成就。在《日本書紀》中也有記載:“朕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朕不自決,乃歷問群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看,可禮以不。”7而飛鳥時代的佛像,亦稱爲飛鳥佛,主要受到中國北魏和南梁樣式的影響。其中,鞍作鳥(止利佛士)一派所造佛像深得北魏樣式精髓,以其莊嚴表情中透露出古樸微笑的特點著稱,給人以超現實的、象徵意義的感覺。例如,飛鳥寺的釋迦如來像、法隆寺金堂的釋迦三尊像、法隆寺夢殿的救世觀音像等(如圖1、圖2、圖3所示)。

圖1 飛鳥寺釋迦如來像

圖2 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像

圖3 法隆寺夢殿救世觀音像
南梁佛像則給人以温和崇高的感覺,例如法隆寺的百濟觀音像等(如圖4所示)。此外,南梁造像風格中帶有寫實特質的還有中宫寺、廣隆寺的半跏思惟像等(如圖5、圖6所示)。

圖4 法隆寺百濟觀音像

圖5 中宫寺半跏思惟像

圖6 廣隆寺半跏思惟像
不過,對於佛教的接受,飛鳥朝廷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以蘇我稻目爲代表的崇佛派和物部尾輿爲代表的廢佛派,因此,在欽明天皇詢問是否舉行佛教儀式的問題上,“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臣尾輿、中臣鐮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這恒一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爲事,今方改拜蕃神恐至國神之怒”8。圍繞崇佛與廢佛問題,蘇我氏與物部氏的激烈鬥争延續到他們的子孫一代,爲了剷除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的勢力,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連同聖德太子一起討伐物部氏。其間,聖德太子發願:“今若使我勝敵,必當奉爲護世四王起立寺塔。”9蘇我馬子也發誓言:“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衛我,使獲利益,願當奉爲諸天與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寶。”10隨著廢佛勢力被剷除,崇佛之風日益興盛。不少王族、豪族爲了顯示其政治權威,修建氏寺。於是,蘇我馬子于558年興建飛鳥寺(法興寺),聖德太子于593年建立難波的四天王寺,607年建立斑鳩寺(法隆寺)。與此同時,聖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進行政治改革。在憲法十七條中,聖德太子强調“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11。此外,聖德太子還將595年高句麗僧人慧慈、百濟僧人慧聰稱爲“三寶之棟梁”。從蘇我馬子的誓言、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等來看,佛教“三寶”的思想深入推古朝廷的貴族階層。根據《上宫聖德法王帝説》的記載:
上宫王師高麗慧慈法師,王命能悟涅槃常住五種佛性之理,明開法華三車權實二智之趣,通達維摩不思議解脱之宗,且知經部薩婆多兩家之辨,亦知三玄五經之旨,並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華等經疏七卷。12
聖德太子精通《涅槃經》《法華經》《維摩經》等,深知佛性之理 13、一乘真實三乘方便 14、不二法門 15,這些都是大乘佛教中極爲精深的佛理;此外,他還認識到小乘佛教中經量部與薩婆多部二者的思想分歧。可見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對當時的日本社會,特别是貴族階層産生了重要影響,其中聖德太子就對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佛理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和理解。而最能代表聖德太子對佛理認識和理解的莫過於《三經義疏》,即《法華義疏》《勝鬘經義疏》《維摩經義疏》。《三經義疏》實際就是對《法華經》《勝鬘經》《維摩經》三部佛經的注解,體現了聖德太子對佛理的基本認識和理解。
除了《三經義疏》之外,能够進一步反映聖德太子佛教思想的是“天壽國繡帳”。根據《上宫聖德法王帝説》記載:“太子崩。于時多至波奈大女郎悲哀歎息,畏天(皇前曰,啓)之雖恐,懷心難止,使我大王與母王如期從遊,痛酷無比。我大王所告,世間虚假,唯佛是真,玩味其法,謂我大王應生於天壽國之中,而彼國之形,眼所叵看,悕因圖像,欲觀大王往生之狀。天皇聞之,悽然一告曰,有一我子所啓,誠以爲然。敕諸采女等,造繡帳二帳。”16聖德太子死後,他的王妃橘大郎女許願希望能够看到聖德太子往生的净土世界。於是,推古天皇就命令宫女製作了兩張繡帳,而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有中宫寺所藏的“天壽國繡帳”殘片“天壽國曼荼羅(如圖7所示)。

圖7 中宫寺所藏“天壽國繡帳”殘片“天壽國曼荼羅”
關於“天壽國曼荼羅銘文”中“天壽國”的含義,目前學界存在諸多争論,諸如西方净土説、兜率净土説等,其中以西方净土説居多。對此,常盤大定基於中國佛經中“天壽國”的用例對“天壽國曼荼羅銘文”中“天壽國”的含義進行了詳盡的考察。爲了説明“天壽國”的含義,常盤大定首先以《維摩經義疏》中的“無量壽經”的“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作爲引證,指出這兩句出自法藏菩薩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從而判斷聖德太子應該精通“無量壽經”,特别是重視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接著,常盤大定以三井家所藏北魏延昌二年(513)手寫《華嚴經》爲佐證。在該《華嚴經》第四十六卷中附有隋開皇三年(583)宋紹演添加的識語。識語内容如下:
大隋開皇三年歲在癸卯五月十五日,武侯帥都督前治會稽縣令宋紹演,因遭母喪,亭私治服,發願讀華嚴經一部,大集經一部,法華經一部,金光明經一部,仁王經一部,藥師經册九遍,願國主興隆,八表歸一,兵甲休息,又願亡父母,託生西方天壽國,常聞正法己身福慶從心,遇善知識,家眷大小康體,一切舍生,普蒙斯願。
在常盤大定看來,開皇三年正值聖德太子十歲之時,所以聖德太子往生的“天壽國”與《華嚴經》識語中的“西方天壽國”含義應該一致。最後常盤大定又調查了北魏、北齊、北周、梁、隋的表示往生信仰的造像銘文五十六例,其中明確表示西方往生的有二十七例。基於上述考察,常盤大定認爲“天壽國曼荼羅銘文”中“天壽國”的含義應該是指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17。但是,末木文美士指出這裏的極樂净土並非後來的净土信仰中純粹的阿彌陀信仰 18。由此可見,關於聖德太子的佛教思想的研究是一個极其複雜的課題,但是無論是“天壽國繡帳”,還是《三經義疏》,它們共同反映了佛教經書典籍在飛鳥時代的傳播狀況,標誌著佛教文明對日本飛鳥時代貴族社會的影響。
二、《三經義疏》的真僞與“絲綢之路”的傳播意藴
關於《三經義疏》的真僞,目前中日學界存在諸多争議。花山信勝詳細分析了明治十一年(1878)法隆寺進獻給日本皇室的“御物”《法華義疏》四卷卷子本,指出該四卷寫本是聖德太子的親筆,其依據有二:一是《法華義疏》中的加筆、修正較多,漢文表述不够確切,符合聖德太子的筆法和漢文水準;二是奈良時代的史料就有關於聖德太子與《三經義疏》的記載,且注解還顯示出對大陸學者的批判之意,顯示出著者水準極高的佛理學識 19。而對於《勝鬘經義疏》,花山信勝則根據奈良時代及之後的相關記載對《勝鬘經義疏》的傳承進行了考證,同時他還分析了現行《勝鬘經義疏》刊本的傳承、校勘問題,論證了《大正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的古注與慧遠、吉藏兩種注解的相同點,進而得出《勝鬘經義疏》是聖德太子親撰之作的結論 20。大野達之助根據《三經義疏》引用的經論注解較爲貧乏,斷定這與推古朝傳入的佛教經卷不多有關,同時他還指出《三經義疏》所引用注解均出自六朝以前,不涉及隋朝以後的經書21。此外,楊曾文還指出《三經義疏》除了引用南朝梁代成實、法雲的《法華義記》和《勝鬘經》注解外,還援引後秦僧肇的《注維摩詰經》以及法空、中公的《維摩經注》等 22。
關於“御物”《法華義疏》四卷卷子本,其成書之初並無書名和作者署名,但後又在第一卷的卷頭處另粘其他紙張題“法華義疏”書名,書名下方又另題“此是大委國上宫王私集非海彼本”,文中有不少其他筆迹的修改(如圖8所示)。

圖8 《法華義疏》卷頭
在注解方面,《法華義疏》“安樂行品”對“常好坐禪”的解釋爲“常好坐禪少(小)乘禪師”,認爲山中坐禪是小乘禪師的修行,是菩薩不該親近的十種對象之一。這種解釋完全與《法華經》本義和法雲《法華義記》的注解不同,因此《法華義疏》顯現出主張超越“大乘”的絶對“一大乘”的特點。對此,末木文美士認爲《法華義疏》强烈地體現了主張在家進行佛教實踐,反對離開世俗生活的山中修行,顯示了推古朝佛教重視在家實踐的重要傾向 23。但是,根據《上宫聖德太子補缺記》記載:“戊辰年(推古十六年,608)九月十五日,閇大殿户,七日七夜,不召群臣,又不御膳,夫人已下不得近習,時人太異。法師曰,太子入三昧定,宜勿奉驚。八日之旦,御機之上有法華一部,驚深加恭敬,出自定後,常有口遊曰,可怜可怜,大隋國僧我善知識,好好讀書,不讀書非爲君子。是敕戒之辭。太子薨後,王子山代大兄,日夜六時禮拜此經。癸卯年十月廿三日夜半,忽失此經不知所去,王子大怪,復以大憂。[今在經者,小野妹子所持也。事在太子傳。]”24另按照《日本書紀》所載:“十六年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25結合《日本書紀》和《上宫聖德太子補缺記》的記載可知,小野妹子作爲遣隋使歸國返日是在推古十六年四月,而同年九月聖德太子用七天七夜的時間埋頭苦讀小野妹子從中國帶回的《法華經》。而津田左右吉出於對《日本書紀》和《上宫聖德法王帝説》所載聖德太子事蹟的質疑,指出:“關於現在流傳下來的《三經義疏》是否真的是聖德太子著作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其他方面的研究進行探討,那就是義疏的注解在中國從六朝末期到隋唐的三經解釋歷史發展過程中到底處於什麽樣地位問題,但是對此我們幾乎不能提供任何具有決定性的文獻材料。《法華經義疏》雖然援引光宅法雲的學説,但却没有涉及提婆品,同時也完全看不到與太子同時代的著名天台僧人智顗的思想。整體而言《法華經義疏》給人一種極爲原始的感覺。”26
較之于津田左右吉的質疑和推測,從事敦煌寫本研究的藤枝晃的成果將我們導向了另外一個思考《三經義疏》的新路徑。藤枝晃指出《法華義疏》的用紙是中國南朝隋系黄褐色的薄麻紙,字與字之間的格子綫與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卷子本一樣,承襲了隋朝卷子本的形制和規格。因此,藤枝晃認爲《法華義疏》是中國的寫經生所寫,而非聖德太子的手書。一般而言,敦煌寫本分期主要爲(1)北朝時期(5—6世紀)、(2)唐朝時期(7—8世紀)、(3)吐蕃·歸義軍時期(9—10世紀)。而敦煌寫本的形制、規格以及内容也各有其特點,其中北朝時期的寫本主要是6世紀末隋朝統一中國之前,採用北朝所特有的紙張,使用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字體寫成的;隨著隋朝統一中國,就又出現了在薄麻紙上用楷書完成的南朝系列寫本。目前,北京、倫敦、巴黎等收藏的敦煌寫本群中,有十件《勝鬘經》的注解文獻是在北朝時期到隋朝之間完成的著作,且都是北朝紙張、字體書寫的卷子本,只有慧遠《勝鬘義記》下卷(613)一件是用南朝紙張、楷書書寫的隋朝著作。根據藤枝晃的統計,目前現存《勝鬘經》注解文獻如表1所示。在敦煌寫本群中,E本《勝鬘經義疏本義》與G本《勝鬘經義疏》在注解上極爲接近,藤枝晃指出二者不僅在注解内容上有七成近似,而且在《勝鬘經義疏》中也稱爲“本義”27。
表1 目前現存《勝鬘經》注解文獻一覽,出自藤枝晃《勝鬘經義疏》

在藤枝晃看來,文獻的改修往往是按照當下的學術風格對前一個時代的名著進行的改編,而隋朝長安、洛陽或者建康等佛教中心地區的一流、甚至是二流學者都有可能在整體理解一本著作的價值後,按照最新的學術動向在幾種注解文獻的基礎上重新提出新的見解。於是,藤枝晃又提出了一系列疑問,他認爲假如是在日本對《勝鬘經》進行的改修,那麽爲什麽只有改修效果不是很好的G本《勝鬘經義疏》流傳至今,而隋朝的重要版本E本《勝鬘經義疏本義》却没有流傳於世,與其他文獻相比,E本《勝鬘經義疏本義》應該更加珍貴。與此同時,藤枝晃還指出不少關於《勝鬘經義疏》的研究往往忽視了奈良時代對佛理的理解水準。他認爲遣隋使本來就肩負著從中國輸入學術文獻的使命,而之所以遣隋使没有將注解水準更高的H本慧遠的《勝鬘義記》帶回日本,正是因爲G本《勝鬘經義疏》與《法華義疏》《維摩經義疏》一樣都是簡略版本,更加適合修習佛理者。於是,藤枝晃認爲《勝鬘經義疏》與《法華義疏》《維摩經義疏》都有可能是遣隋使帶回日本的注解文獻 28。
關於藤枝晃的觀點,末木文美士評價説:“如果藤枝晃的考證是正確的,那麽站在日本史的立場上,視本書爲重要書籍之事,將變得毫無意義。在敦煌寫本研究的這一個新實證性的研究領域成果上,藤枝晃提出的主張是極重要的。至目前爲止,尚未看到主張真撰的人提出有力的反論。”29可見,藤枝晃的考證對於聖德太子的《三經義疏》的真僞問題是極具衝擊力和壓倒性的。而末木文美士的言外之意是藤枝晃的“敦煌説”爲認識漢化佛教東傳日本提供了另外一種視野—“絲綢之路”的傳播史。
三、從敦煌到奈良—延伸到海上的“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史
日本作家井上靖根據“大宋國潭州府舉人趙行德”的史料虚構了一個敦煌千佛洞的歷史軌迹。在1959年《敦煌》單行本刊印的時候,負責題籤和裝幀的正是前文我們提到過的著名“絲綢之路”專家藤枝晃,他選取了西夏經的一部分,以西夏文字表記的沙洲作爲封面,以莫高窟的元代“六體文字碑”作爲扉頁30。這塊“六體文字碑”即敦煌現存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它由梵文、藏文、漢文、西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寫成,六種文字以“唵嘛呢叭咪哞”爲音,六字真言爲觀音菩薩咒。由此可見敦煌與佛教之間的緊密關係。那麽,敦煌之於佛教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佛教在公元1世紀由印度傳到東漢時期的中國,經洛陽“釋源”白馬寺向東亞傳播。5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北方在北魏的統治下興建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南朝則貴族佛教興盛,隋朝統一南北後,隋文帝、隋煬帝大興佛教,擊敗突厥和吐谷渾的侵擾後在瓜州崇教寺起塔,敦煌大興開窟之風 31。敦煌距離隋唐西都長安有一千三百多公里,距離東都洛陽一千六百公里,不僅佛教興盛,而且是“絲綢之路”連接東西文化的要衝。一般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是從洛陽或者長安出發進入蘭州,經武威、張掖、酒泉,通過河西走廊抵達敦煌,以敦煌爲交叉點分爲南北兩條幹綫。現存的敦煌文獻中大約九成都是佛教文獻,尤以漢文文獻最多。换句話説,敦煌不僅是東西文明的交匯點,更是佛教漢化的紐帶。
從敦煌展開的“絲綢之路”承載了漢化佛教不斷東漸的文化傳播史意義。對于藤枝晃提出的《三經義疏》“敦煌説”,近年來石井公成通過對《三經義疏》語法的分析,指出其與真正的漢文存在齟齬之處,而混雜“倭習”的變異體漢文語法反而與《日本書紀》等相似,提出了“敦煌説”的反論 32。即便如此,丸山裕美子通過對“御書”聖武天皇的《雜集》、元正天皇的《孝經》以及光明皇后的《杜家立成》與敦煌寫經關係的考察,指出“在這裏我想關注的是御書與中國敦煌寫本的相似性。光明皇后的《杜家立成》與《雜集》是流傳至正倉院的御書,它的書儀我在之前已經提到過,可以在敦煌寫本中發現100處以上的相似點。元正天皇的《孝經》内容也與敦煌寫本一致。而且聖武天皇《雜集》中的净土詩、佚名作品以及《鏡中集》的齋文、願文也殘存在敦煌寫本之中”33。在此基礎上,王三慶對聖武天皇《雜集》中收録的《奉讚净土十六觀詩》《隋大業主净土詩》《奉王居士請題九想即事依經總爲一首》等部分與敦煌文獻之間的關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比較研究,指出“《雜集》中的其他文字不但可與敦煌文獻從事一東一西的遥相呼應,更保留了中土已經亡佚的作品”34。雖然丸山裕美子、王三慶的研究没有涉及《三經義疏》與敦煌寫經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研究却進一步佐證了敦煌佛教文獻在日本的傳播。於是,沿著“敦煌説”所提供的“絲綢之路”視野我們可以將文化意象的漢化佛教傳播從敦煌延伸至奈良,從而形成了“絲綢之路”的佛教文化傳播過程。根據《隋書》《日本書紀》的記載,來自日本的遣隋使分别在隋文帝(600)、隋煬帝(607)時抵達長安、洛陽 35,他們在遞交國書的同時搜集相關典籍文獻。或許敦煌文獻就是在與遣隋使的文化交匯中促進了漢化佛教的傳播。目前,史料所載遣隋使情況大致如表2所示。
表2 遣隋使情況表,參照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36

(續表)

關於遣隋留學生、留學僧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問題,楊曾文認爲:“其中學問僧有八人,約占全部人數的62%。可以説,在推古朝派到隋朝留學的人是以學習佛法爲主,同時兼學中國政教文化。”37木宫泰彦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認爲在二三十年間,遣隋的留學生、留學僧不僅學習佛教、儒學,還通過各種見聞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産生了深遠影響38。整體而言他們都肯定了這些遣隋留學生、留學僧對於日本推古朝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意義。當我們把佛教傳播射程投向之後的五山禪林甚至江户儒學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些遣隋的留學僧身上早就打上儒釋二道相互融合的特質。根據《日本書紀》記載,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自學周孔之教于南淵先生所”39,而且“按推古天皇十六年紀,所謂學問僧南淵漢人請安是也,按此時釋氏兼儒,如孝德天皇之時,旻法師任國博士是也,由是觀之,請安亦兼得周孔之教,故稱先生”40。由此可見,無論是僧旻還是南淵請安,他們從隋朝返回日本後的這種“釋氏兼儒”的學問特質也得到當時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等貴族的接受,爲後來的“乙巳之變”和“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礎。而之所以遣隋留學僧的這種特質能够爲推古朝的貴族所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是“釋氏兼儒”體現出了相當强的實學性意義。上文我們提到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他們在“乙巳之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都曾參加留學僧南淵請安的儒學講堂。而僧旻在632年從隋朝歸國後開堂講授《周易》,蘇我入鹿和中臣鐮足也都曾參加過他的講堂。特别是637年2月日本出現了“大星從東流西,便有音似雷”的現象,僧旻解釋説“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聲似雷耳”;“乙巳之變”之後,他又以國博士的身份參與孝德朝的政治活動,並通過引用中國古典以祥瑞之由改元白雉 41。從僧旻、南淵請安返回日本後的影響來看,這些費盡千辛萬苦遣隋的留學僧反而從事的是講授儒學的工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留學僧就不從事弘揚佛法的工作了,例如舒明天皇十二年的時候,留學僧惠隱就爲天皇講解《無量壽經》42。不過,對於留學僧的作用,目前學界也存在諸多争議,森公章就認爲留學僧所學的並不是最新的隋唐政治制度,而是隋唐之前的北朝制度 43。但是,當我們把遣隋留學僧的佛學、儒學等當作“知識”來看的話,會發現他們對佛教、儒學等的理解符合知識性的認識過程,顯示出他們的學問構成具有知識性的一面。即便如此,作爲“知識”的佛學、儒學等在留學僧回國以後仍然通過他們合理化的解釋應用到日本政治社會的建設之中。這顯示了佛教、儒學在傳入日本後産生了一種嶄新的實學屬性。這一傾向在之後遣唐的留學僧身上表現得更爲突出。
遣唐使肇始于舒明二年(630),廢止于寬平六年(894),共計二十次,關於遣唐使的出使情況,木宫泰彦、石井正敏等學者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本文在木宫泰彦和石井正敏的研究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補正(表3)。
(續表)

(續表)

較之于遣隋使而言,遣唐使的規模是空前的,所以它對唐代以後的文化傳播産生了更爲深遠的影響。從表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遣唐使的入唐路綫,即北路與南綫。那麽,如果我們從“絲綢之路”的傳播史視野重新審視遣唐使的入唐路綫的話,是否會進一步擴大我們觀察漢化佛教東傳日本的視野呢?對此,我們首先將探討的問題回到敦煌與遣唐使的入唐路綫的關係上。
遣唐使的入唐路綫,木宫泰彦 46、森克己 47、河内春人 48、馬一虹 49、石井正敏 50等學者都有極爲詳細的研究和考證,主要有北綫與南綫,北綫從北九州經壹岐、對馬,沿著朝鮮半島西海岸北上,横跨黄海抵達山東半島,再經陸路抵達洛陽、長安;南綫則是從筑紫的西岸或者五島列島南下横穿東海抵達長江江口,經陸路抵達洛陽、長安。於是就形成了漢化佛教從敦煌到長安、洛陽再經陸路、海路抵達日本傳到奈良的“絲綢之路”式的文化傳播路徑。
從《三經義疏》、聖武天皇的《雜集》、元正天皇的《孝經》以及光明皇后的《杜家立成》來看,漢化佛教經這一條“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路徑不斷傳入日本。此外,唐代傳入日本的還有六朝古佚本傅亮《光世音應驗記》、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陸杲《繫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而遣唐的留學僧在奈良時代帶回的唐臨《冥報記》則對平安時代的《日本靈異記》産生了巨大影響,根據《日本靈異記》序文:“昔漢地造《冥報記》,大唐國作《般若驗記》,何唯慎乎他國傳録,弗信恐乎自土奇事。粤起自矚之,不得忍寢,居心思之,不能默然,故聊注側聞,號曰《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作上中下參卷,以流季葉。”51序言所提到的“《般若驗記》”即是唐代孟獻忠的《金剛般若集驗記》,日本石山寺現存平安時代前期的抄本上卷,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現存附卷殘卷,奈良國立博物館藏有平安時代承曆三年紙本墨書折本。鄭阿財通過古佚六朝《光世音應驗記》、唐代唐臨《冥報記》、唐代孟獻忠《金剛般若集驗記》探討了日本藏敦煌寫本及古寫本靈驗記的價值 52。可見,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從敦煌傳入日本奈良,並對之後的平安時代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從“絲綢之路”的傳播史意義來看,漢化佛教是連續性地、多元化地從敦煌傳入日本。
四、結論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再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乃至中南半島等東亞國家地區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在中國爲中心的東亞已然形成大範圍的漢字文化圈。换句話説,漢字文化圈的形成爲佛教東漸奠定了基礎。因此,佛教文獻的漢譯成爲其傳播的關鍵。目前關於中國佛教文獻的漢譯根據史料可追溯至東漢桓帝時抵達洛陽從事經文翻譯的安息國安世高、月氏國支婁迦讖。後鳩摩羅什來華,在長安的譯經場西明閣、逍遥園翻譯經文的同時,開講釋法,其中像大乘佛教典籍《大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阿彌陀經》《維摩詰經》,禪觀典籍《坐禪三昧經》《禪秘要法經》等對後來的佛教産生了重大影響。而敦煌作爲東西文明的交匯之地,也是重要的譯經場。根據《三經義疏》、聖武天皇《雜集》、元正天皇《孝經》以及光明皇后《杜家立成》乃至寫本靈驗記等文獻的考察,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從敦煌到奈良這一跨越地理空間的“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史的軌迹。這一軌迹又恰恰是隱藏在漢化佛教東傳日本中的文化意藴。近年來,從文化的視角審視佛教在東亞的傳播逐漸成爲學界關注的焦點,高崎直道、木村清孝編“東亞佛教”系列有《東亞社會與佛教文化》53,如沖本克己編“新亞洲佛教史”系列有《作爲中國文化的佛教》54,超出既有的文獻(document)、藝術(art)、宗教(religion)以及哲學(philosophy)視域下的佛教研究範式,以文化意象重新挖掘隱藏在漢化佛教東傳過程中的傳播史意義。而我們透過漢化佛教從敦煌到長安、洛陽再到奈良的傳播過程,可以明確地認識到通過“絲綢之路”所産生的文化傳播史意義。
1 關於漢化佛像、佛經在日本傳播的研究,主要有:楊曾文,《中華佛教史·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楊曾文,《日本佛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8;藤堂恭俊、塩入良道,『漢民族の仏教:仏教伝来から隋·唐まで』,東京:佼成出版社, 1975;日本仏教研究会編,『アジアの中の日本仏教』,京都:法藏館,1995;目幸黙遷,『飛鳥·奈良仏教:国家と仏教』,東京:佼成出版社,1972;後藤宗俊,『塼仏の来た道―白鳳期仏教受容の様相』,京都:思文閣出版,2008;長岡龍作,『日本の仏像』,東京:中公新書,2009等。
2 關於敦煌佛教與日本佛教的關聯性,主要研究有: 田村圓澄、川岸弘教編,『日本仏教宗史論集第一巻:聖德太子と飛鳥仏教』,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丸山裕美子,『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東京:中公新書,2010;王三慶,《從聖武天皇〈雜集〉的整理研究兼論其與敦煌文獻之關涉》,《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013年第7號等。
3 關於聖德太子《三經義疏》與敦煌寫經關係的研究,主要有:花山信勝,『聖德太子御製法華義疏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仏書林,1978;家永三郎、藤枝晃、築島裕,日本思想体系2『聖德太子集』,東京:岩波書店、1975等。另有:花山信勝「三経義疏について」、藤枝晃「北朝における勝鬘経の伝承」、井上光貞「三経義疏成立の研究」,收入田村圓澄、川岸弘教編,『日本仏教宗史論集第一巻:聖德太子と飛鳥仏教』,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等。
4 仏書編行会編纂,『大日本仏教全書』「元興寺縁起」,東京:仏書編行会,1913,137頁。
5 仏書編行会編纂,『大日本仏教全書』「元興寺縁起」,138頁。
6 坂元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貞、大野晋,『日本書紀下』卷第十九,東京:岩波書店, 1965,101頁。
7 『日本書紀下』卷第十九,101—103頁。
8 『日本書紀下』卷第十九,103頁。
9 『日本書紀下』 卷第二十一,163頁。
10 『日本書紀下』卷第二十一,165頁。
11 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条』,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1頁。
12 塙保己一,『群書類従第四輯巻第六十四:上宫聖德法王帝説』,東京:経済雑誌社, 1898,333頁。
13 佛性之理是指《大涅槃經》所講佛身常住,衆生皆有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緣因佛性、果佛性、果果佛性五種佛性。
14 一乘真實三乘方便是指《妙法蓮華經》所謂聲聞、緣絶、菩薩三乘爲佛的方便之教。
15 不二法門是《維摩詰經》中“不可思議解脱法門”,所謂“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爲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脱門即是三解脱門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16 塙保己一,『群書類従第四輯巻第六十四:上宫聖德法王帝説』,336頁。
17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の研究』「天壽国について」,東京:春秋社松柏館,1938, 201―207頁。關於常盤大定的“西方天壽國”論述,大屋德城認爲常盤大定對識語的識讀有誤,應該是“無”字而非“天”字,所以識語應該是“西方無壽天”。詳細參照:大屋德城,「最近の天壽国問題に就いて」,『密教研究』1939年第70號,40―41頁。
18 末木文美士,『日本仏教史―思想史としてのアプローチ』,東京:新潮社,2001,38頁。
19 花山信勝,『聖德太子御製法華義疏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仏書林,1978。另參照花山信勝,『法華義疏の研究』二卷,東京:東洋文庫叢刊第18,1933。
20 花山信勝,『勝鬘経義疏の上宫王撰に関す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4,468頁。
21 大野達之助、中村元,『新稿日本仏教思想史』,東京:吉田弘文館,1973。關於《三經義疏》引用的佛經文獻主要是《法華義疏》引用了《無量義經》《般若經》《涅槃經》等,《勝鬘經義疏》提及《法鼓經》《優婆塞戒經》《涅槃經》《般若經》等,《維摩經義疏》則涵蓋了《無量壽經》《乳光經》《釋論》。
22 楊曾文,《日本佛教史》,31頁。
23 末木文美士著,涂玉盞譯,《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12頁。
24 塙保己一,『群書類従第四輯巻第六十四:上宫聖德法王帝説』,341頁。
25 経済雑誌社,『日本書紀巻二十二』,東京:秀英社,1897,382頁。
26 津田左右吉,『日本上代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0,197―198頁。
27 家永三郎、藤枝晃、築島裕,日本思想体系2『聖德太子集』,東京:岩波書店,1975, 486—488頁。
28 日本思想体系2『聖德太子集』,538—539頁。
29 末木文美士著,涂玉盞譯:《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13頁。 另參照末木文美士:『日本仏教史―思想史としてのアプローチ』,43頁。
30 礪波護,『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京都:法藏館,2016,30頁。
31 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岡秀友,『アジア仏教史·中国編V シルクロードの宗教』,東京:佼成出版社,1975,156頁。關於敦煌石窟的研究,中日兩國學界在夏鼐、宿白、長廣敏雄、岡崎敬等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分别由中國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了大型系列叢書《中國石窟》十七卷,其中《敦煌莫高窟》五卷。參文物出版社、平凡社共編,《中國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990。
32 石井公成,「三経義疏の語法」,『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008年第57卷第1號,43—49頁。
33 丸山裕美子,『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東京:中公新書,2010, 23—24頁。
34 王三慶,《從聖武天皇〈雜集〉的整理研究兼論其與敦煌文獻之關涉》,《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013年第7號,7—22頁。
35 關於第一批遣隋使的記載有兩種,一種是《隋書·倭國傳》記載爲開皇二十年(600),另一種是《日本書紀》記載爲推古十五年(607),王勇認爲遣隋使始於公元600年較爲妥當,參照王勇:《從遣隋使到遣唐使》,《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96頁。日本史學界也採用了《隋書》的説法,參照佐藤信、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詳説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12,50頁。另參照家永三郎、藤枝晃、築島裕,日本思想体系2『聖德太子集』,538—539頁。
36 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京都:冨山房,1962,70頁。
37 楊曾文,《中華佛教史·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32頁。
38 參照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71頁。
39 『日本書紀下』巻第二十四,255頁。
40 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73頁。
41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舒明天皇“九年春二月丙辰朔,戊寅,大星從東流西,便有音似雷。時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於是,僧旻僧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聲似雷耳”;孝德天皇白雉元年“二月庚午朔,戊寅,穴户國司草壁連丑經獻白雉曰,國造首之同族贊。(中略)僧旻法師曰,此謂休祥足爲希物。伏聞,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又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又王者清素則山出白雉,又王者仁聖則見。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白雉曰,吾聞,國之黄耇曰,久矣無别風淫雨,江海不波溢三年於兹矣,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故重三譯而至。又晉武帝咸甯元年,見松滋是休祥,可赦天下,是以白雉使放於園”。詳細參照『日本書紀下』卷第二十三、二十五,231—233頁、313頁。
42 《日本書紀》記載,(舒明天皇)十二年(中略)五月丁酉朔,辛丑,大設齋,因以請惠隱僧,令説無量壽經。詳細參照『日本書紀下』巻第二十三,235頁。
43 森公章,「遣隋·遣唐留学者とその役割」,『専修大学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学報』2010年第4號,93頁。
44 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74—81頁。
45 石井正敏著,村井章介、榎本渉、河内春人編,『石井正敏著作集第二巻遣唐使から巡礼僧へ』,東京:勉誠出版,2018,20—31頁。
46 木宫泰彦,『日華文化交流史』,90—96頁。
47 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編集委員会,『新編森克己著作集第2巻:続日宋貿易の研究』,東京:勉誠出版,2009,68頁。
48 河内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東京:汲古書院,2013,55—62頁。
49 馬一虹,「円人入唐求法の山東行程に関する考察」,佐藤長門編,『遣唐使と入唐僧の研究―附校訂「入唐五家伝」』,東京:高志書院,2015,91—110頁。
50 『石井正敏著作集第二巻遣唐使から巡礼僧へ』,13—14頁。
51 武田祐吉,『日本霊異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61,264頁。
52 鄭阿財,《論日本藏敦煌寫本及古寫經靈驗記的價值》,《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 23—50頁。
53 高崎直道、木村清孝編,『シリーズ東アジア仏教:東アジア社会と仏教文化』,東京:春秋社,1996。
54 沖本克己編,『新アジア仏教史:中国文化としての仏教』,東京:佼成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