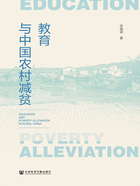
二 反贫困相关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贫困的内涵及外延
1.贫困的内涵
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消除贫困,实现人类全面发展,是人类追求的共同愿望。从国内外来看,关于贫困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必然产物,但是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贫困定义。后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较早地提出了贫困的定义,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人是穷还是富,主要由他能够享有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等的多少决定。此后,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对贫困的定义也越来越广泛,如英国学者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在1901年出版的《贫穷: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一书中提到,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总收入水平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即为贫困(Rowntree,1901;王小林,2012)。朗特里首次从收入(物质)视角对贫困进行了定义,这一经典的定义为后续人类研究贫困开了先河,将贫困问题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在1963年开始用收入定义美国的贫困(Orshansky,1963;王小林,2012)。
贫困实际上是一个模糊、宽泛的概念,随着人们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入,贫困的概念也愈加广泛,逐渐从“生存”视角延伸到“发展”“能力”等视角。Goedhart、Halberstadt和Kapteyn(1977)认为贫困就是在购买实物、服务等方面缺乏可支付能力。汤森德(Townsend,1982)则提出了“资源缺乏贫困论”,并且认为贫困是“资源分配不平等导致的生活相对困难状态”。英国学者奥本海默(Oppenheim)却将贫困定义为物质上、精神情感上的匮乏,同时也表现为食物、衣着、住房等方面的开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同时它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姚云云和班保申,2016)。后来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人口由于机会的缺失和基本生存能力被剥夺,无法从外部获取收入以支持自身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Sen,1976)。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贫困并不仅表现为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和基本能力有着密切联系。基本能力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营养不良、受教育水平低、健康状况差、过早死亡以及不能享受医疗服务、没有政治参与权等。因此,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需要将目光投入教育、健康等基本生存需要,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能力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随后,贝弗里奇(2004)将“疾病、匮乏、无知、肮脏”等定义为贫困,阐述了贫困人口在教育、住房、医疗、食物等方面的缺失状况。
在国内,不少学者也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如周彬彬(1991)认为贫困就是经济收入低于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标准要求。童星和林闽钢(1994)指出贫困应该是经济、文化、社会落后的总称,是由收入水平低下造成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康晓光(1995)认为贫困代表一种生存状态,如果个人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参加社会活动机会难以获得,就会导致个人在社会文化和生理上的基本生活状态无法维持。樊怀玉和郭志仪(2002)将贫困定义为由收入不足导致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状况。唐玉凤、黄如兰和吴娜(2008)则从相对含义视角出发,将贫困人口定义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冯贺霞、王小林和夏庆杰(2015)从基本需求和基本能力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内涵,并且对两者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诸多学者结合贫困的不同内涵从多种角度展开了大量研究(Duncan and Rodgers,1991;Bayudan-Dacuycuy and Lim,2013;Libois and Somville,2018;程名望、Jin Yanhong和盖庆恩等,2014;王春超和叶琴,2014;郭熙保和周强,2016;贺立龙、黄科和郑怡君,2018)。
综合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的概念和度量在学术界逐步深化和完善,由最开始的收入贫困发展到后来的能力贫困,再到权利贫困。贫困的内涵界定也一直在不断变化,这也说明了贫困并不只是收入(物质)上的缺乏,也应该包括物质资本以外的非物质资本的缺乏。因此,贫困应该具有相对性、多维性等特征(周强,2017)。
2.贫困的层次性
按照研究层次的不同,贫困又可以分为宏观贫困、中观贫困以及微观贫困。其一,宏观贫困主要从国家层面出发,探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做国家之间的贫困对比分析等(张克中和郭熙保,2009)。其二,中观贫困主要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的贫困情况,如农村贫困、城市贫困、县域贫困、村(镇)贫困等。其三,微观贫困主要以家庭或者个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内部或者个人的贫困情况。对这三个层面的贫困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的理解,以下我们分别对这三个层面的贫困做简要梳理。
首先,宏观贫困。这类研究相对较早,最初对贫困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展开的,并且形成了很多关于贫困的理论,如大推进理论、低水平均衡理论、不均衡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基本都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又比如舒尔茨在出版的《穷国的经济学》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穷国落后的原因等。Alkire、Roche和Vaz(2017)在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后,对比分析了34个国家多维贫困的变化情况。同年,Fosu(2017)以发展中国家为考察对象,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贫困减缓,但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了贫困程度,因此他强调发展中国家要重视收入不平等问题。后来,Inoue(2018)探讨了1980~2013年全球120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对贫困的影响。中国学者江刚(2001)发现全球气候变暖对穷国的影响最大,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国家往往依赖传统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加上这些国家又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措施和能力,因此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胡晓山(2005)则指出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起的“重债穷国计划”理论上能够减轻受援国的债务负担,并通过增加穷国的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受到很多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个计划的实际价值并没有那么大。尚卫平和姚智谋(2005)分析了多维贫困的测度方法,并且测度比较了国家之间的贫困程度。也有学者基于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变化视角审视了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胡兵、赖景生和胡宝娣,2007)。张克中、冯俊诚和鲁元平(2010)则以公共支出结构和效率为出发点,探析了财政分权对贫困的影响。王弟海(2012)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发现富国具有高资本、高健康和高消费水平,而穷国正好相反。而蔡昉(2013)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嵌入相应的增长类型和阶段,如“李约瑟之谜”“刘易斯转折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祁毓和卢洪友(2015)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其次,中观贫困。中观贫困的研究通常从县域、村级或者地区层面展开,成果相对较多。如翟荣新和刘彦随(2008)以云南省73个国定贫困县为例,探析了这些国定贫困县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做了因子分析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袁媛、王仰麟和马晶等(2014)则构建了包含经济维度、自然维度、社会维度等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河北省136个县的贫困状况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度的评估。近年来,随着“连片特困区”的提出,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连片特困区的贫困情况,如丁建军(2014)基于综合发展指数计算视角研究了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而邹波、张彬和柴盈(2016)则分析了中国连片特困区的绿色贫困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贫困村分类瞄准的机制(邓维杰,2013)。就中国而言,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现象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分布在西部地区。对此,不少学者针对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如童玉芬和尹德挺(2009)发现西北部地区贫困人口总量大,生态贫困状况严重,而且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据较高比重;并且民族地区贫困呈现“空间陷阱”特征(张丽君、董益铭和韩石,2015)。加上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之间的贫困差异问题也不容忽视,诸多研究表明城市和农村贫困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且呈现动态、复杂性的特征(王美昌和高云虹,2017)。
最后,微观贫困。微观贫困研究家庭或者个体的贫困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贫困问题更加具体,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精准有效。由于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存在贫困家庭或者个体,只是贫困程度的高低存在差异而已(张莹和万广华,2006)。国家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思想,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贫困家庭、贫困个体(居民)的重视。因此,研究微观贫困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避免了“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地区大扶贫政策下的弊端,使得扶贫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精准有效(周强,2017)。由于从微观层面研究贫困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综合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特点,因此受到了诸多学者的青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微观调查数据平台的快速发展,很多微观数据免费对外公开,采用微观数据分析家庭或者个人贫困的文献日益增多(Chakravarty,Mukherjee and Ranade,1998;Mcculloch and Calandrino,2003;Yu,2013;Li and Sicular,2014;Ghalib,Malki and Imai,2015;Zhang,Zhou and Lei,2017;Hou,Liao and Huang,2018)。例如,Fan、Gulati和Thorat(2008)采用印度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经济增长对家庭贫困的影响。而Imai、Arun和Annim(2010)则利用印度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家庭贫困的影响。夏庆杰、宋丽娜和Simon Appleton(2007)利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数据估算了中国1988~2002年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张雪梅、李晶和李小云(2011)对2000年以来中国妇女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进行研究评述和展望。蒋翠侠、许启发和李亚琴(2011)则对多维贫困指数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并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做了实证分析。洪兴建和邓倩(2013)利用CHNS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王春超和叶琴(2014)基于收入和教育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而张川川、John Giles和赵耀辉(2015)则评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程度;同年,解垩(2015)采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对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王美昌和高云虹(2017)则利用中国综合和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贫困发生率。此外,国内学者姚毅(2012),樊丽明和解垩(2014),向运华和刘欢(2016),樊士德和江克忠(2016),刘一伟和汪润泉(2017),侯亚景和周云波(2017),谭燕芝、张子豪和眭张媛(2017)等借助CHNS、CFPS、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等具有代表性的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贫困发生率及其动态变化状况。
总体来说,宏观贫困、中观贫困以及微观贫困虽然具有差异性,但是三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宏观贫困强调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而中观贫困强调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微观贫困则强调以家庭、个体为研究对象。对三者的了解可以加深对贫困的认识。
3.贫困的静态性与动态性
从现有关于贫困的研究来看,目前绝大多数研究将重点放在特定时间的贫困,即静态贫困上。按照Chaudhuri和Ravallion(1994)的解释,静态贫困可以理解为家庭或者个人在特定时点上的贫困状态。有关静态贫困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Addabbo and Baldini,2000;张莹和万广华,2006;张克中、冯俊诚和鲁元平,2010;程名望、Jin Yanhong和盖庆恩等,2014;陈飞和翟伟娟,2015;温涛、朱炯和王小华,2016;王小华、王定祥和温涛,2014)。虽然静态贫困研究能够识别贫困状态,但是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无法进行动态分析(Ravallion,1988;Rodgers and Rodgers,1993;Hulme and Shepherd,2003;Duclos,Araar and Giles,2010;Wan and Zhang,2013;Fujii,2017)。静态贫困研究只能分析特定时点上的贫困状态,不能给出一段时间内贫困的变化情况,更不能回答家庭或个人何时陷入贫困,何时脱离贫困,以及贫困持续时间有多长等问题(李小云、张雪梅和唐丽霞,2005;周强,2017)。
据此,从动态层面分析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观察贫困的动态性(Jalan and Ravallion,1998;Baulch and Masset,2003;Hoy and Zheng,2011;Wan and Zhang,2013;Ward,2016),并试图将时间因素纳入贫困的分析框架中,使得贫困分析具有了时间因素。Bane和Ellwood(1986)是较早开始研究动态贫困的学者。后来,世界银行在2001年提出“贫困的脆弱性”,这其实就反映出了贫困的动态特征。但是,对于如何定义贫困的脆弱性,如何定义动态贫困,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大多从时间维度来研究动态贫困(Jalan and Ravallion,2000;Duclos,Araar and Giles,2010;Bayudan-Dacuycuy and Lim,2013;Alkire,Roche and Vaz,2017)。
从国内研究来看,章元、万广华和史清华(2012)是国内较早从动态视角分析贫困的学者。在他们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以家庭和个人为研究对象,将总体贫困分解为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两种类型,结果发现,考察区域内农村家庭总体贫困状况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慢性贫困相对严重,而暂时性贫困相对缓和,且慢性贫困在总体贫困中所占比重要明显大于暂时性贫困。随后,在2013年,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暂时性贫困下降能够导致总体贫困下降,且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暂时性贫困的作用不明显,但能够有效降低慢性贫困和总体贫困(章元、万广华和史清华,2013)。此外,万广华、刘飞和章元(2014)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对非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慢性贫困等三类贫困的影响。在国内,罗楚亮(2010)、邹薇和方迎风(2011)、叶初升和赵锐(2013)、郭熙保和周强(2016,2017)、侯亚景(2017)等也对动态贫困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测度分析动态贫困,并且对它进行分解;同时,也有个别文献考察影响动态贫困的因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代际贫困也是动态贫困的一种表现形式(Harper,Marcus and Moore,2003;Horii and Sasaki,2012)。由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代际贫困角度分析了动态贫困(谢婷婷和司登奎,2014;卢盛峰和潘星宇,2016)。代际贫困表示父代与子代之间贫困状态的传递,子代贫困往往受到父代贫困的影响。Becker和Tomes(1979,1986)率先通过建立世代交迭模型分析了贫困的流动性。随后,有关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开始增多,如王海港(2005)、郭熙保和周强(2017)等。后来,也有学者将时间因素纳入贫困代际传递研究中,以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长期性,如方鸣和应瑞瑶(2010)、张立冬(2013)、郭熙保和周强(2017)。综合来看,学术界将贫困的研究从静态贫困逐渐延伸到动态贫困和代际贫困,进而转到长期代际贫困,由此可见贫困具有流动性、时间性的特征。
(二)贫困的影响因素
研究贫困的影响因素,是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环节之一。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贫困的决定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视角,分别为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其中,宏观视角主要基于国家政策、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等宏观因素(Balisacan and Pernia,2002;Adams,2004;Fosu,2015);而微观视角主要基于家庭、个体特征和行为等微观因素。就宏观视角而言,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始终贯穿该研究的一条主线(叶普万,2004)。综合国内外文献也可以发现,大量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Dollar and Kraay,2002;Yao,Zhang and Hanmer,2004;Fosu,2017;夏庆杰、宋丽娜和Simon Appleton等,2010;单德朋、郑长德和王英,2015)。在实践中,华盛顿共识所坚信的“涓滴效应”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并且也表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贫困人口。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利于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反而会加大贫困发生率(Son and Kakwani,2008;Fosu,2010;Benjamin,Brandt and Giles,2011;罗楚亮,2012,尹飞霄,2013)。除此之外,不少学者也关注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外的其他影响贫困的宏观因素,如关注FDI与贫困之间的关系(Shamim,Azeem and Naqvi,2014;Magombeyi and Odhiambo,2018)。中国学者刘渝琳和林永强(2011)利用平滑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FDI对中国贫困减缓有显著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而张克中、冯俊诚和鲁元平(2010),储德银和赵飞(2013)关注了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刘晓昀和辛贤(2003),康继军、郭蒙和傅蕴英(2014),汪三贵和王彩玲(2015)则指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缓解农村贫困状态。甚至还有不少学者关注了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Tsai and Huang,2007;张茵和万广华,2007)、气候因素对贫困的影响(Barbier,2015;Zhou,Chen and Li et al.,2017;尹飞霄,2013)。
相比于宏观视角研究而言,微观视角的研究略显单薄,但是随着近年来微观调查数据的增多,从微观视角研究贫困的文献也开始逐渐增加。综合已有文献来看,在研究家庭或个人贫困中,诸多学者考察了人力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一致认为教育、健康等核心人力资本是影响贫困的关键因素(Autor,Levy and Murnane,2003;Bayudan-Dacuycuy and Lim,2013;Libois and Somville,2018;王海港、黄少安和李琴等,2009;章元、万广华和史清华,2012;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王春超和叶琴,2014)。而徐月宾、刘凤芹和张秀兰(2007),程名望、Jin Yanhong和盖庆恩等(2014),郭熙保和周强(2016)则研究了家庭特征对家庭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数量、儿童数量越多,家庭越容易陷入贫困,并且家庭女性成员的占比越高,越有利于家庭摆脱贫困。此外,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刘一伟(2017)还发现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户家庭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更容易摆脱贫困。也有部分学者从农户行为视角出发,研究了农户行为变动对贫困的影响,如Du、Park和Wang(2005),向运华和刘欢(2016)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流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贫困,但是这种缓解效应相对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农村贫困人口的流动性并不大;对于该观点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程名望、史清华和徐剑侠,2006;章元、万广华和史清华,2012)。还有学者认为土地流转越顺利、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家庭摆脱贫困(王春超,2011;侯亚景和周云波,2017)。从村庄视角出发,卢盛峰、陈思霞和张东杰(2015),周强和张全红(2017)发现村庄学校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影响农户贫困状况。
(三)反贫困的方式与手段
反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在反贫困的历程中,形成了诸多反贫困方式。较为典型的反贫困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式扶贫(岳映平,2015)。在识别出贫困的具体情况后,可以根据致贫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反贫困措施。
1.救济式扶贫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历程中,救济式扶贫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贫困方式。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方式之一,救济式扶贫方式主要是为了让贫困居民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毕少斌和刘爱龙,2012)。在救济式反贫困方式中,对贫困居民通常采取的是直接的实物支持或者资金救助,其本质是一种简单的“输血式”反贫困方式(陈标平和胡传明,2009)。
通常情况下,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其总收入水平几乎难以保障当地居民基本的生存需求。为了帮助这些当地居民摆脱贫困状态,国家通常采取直接救济的方式使他们脱贫。其中救济式扶贫的主要手段为对贫困居民予以粮食补贴、实物救助、生活资金补助等,简单来说,即“钱-棉-粮”式的直接援助。一般是直接扶贫到村到户,扶贫的对象相对明确、精准,能够直接满足贫困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由于救济式扶贫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所以一些国家采纳了这一方式。中国学者王延中和王俊霞(2015)强调了社会救助对反贫困的作用。不过,救济式扶贫方式仅仅能够缓解贫困人口的燃眉之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从总体来看,效果不佳(毕少斌和刘爱龙,2012)。这主要是因为接受救济的贫困居民自身缺乏创收的能力或者机会,在受援的实物、资金等资源被消耗完之后,他们又将陷入贫困状态,并未实现真正的脱贫,返贫率很高。同时,救济式扶贫是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支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难以长期支持。毕少斌和刘爱龙(2012)同样指出救济式扶贫会导致贫困居民在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方面出现明显断裂,这在一定层面上也导致其反贫困功效甚微。虽然救济式扶贫能够在特定时间内缓解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但是并不是长久之计。
总体而言,救济式扶贫是一种被动的受援方式,它只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不能从本质上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生产力和生存能力;相反,还可能造成贫困人口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进而形成“等、靠、要”的不健康思想。
2.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的重点放在对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通过改善当地生产条件和发展商品生产等,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旨在通过经济建设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开发式扶贫是相对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缺点而展开的扶贫方式,通过引导贫困地区的人口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开发建设中,把自己的努力与国家扶持有机地结合起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开发式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方式,通过借助外力来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助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陈标平和胡传明,2009)。在开发式扶贫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扶贫手段有绿色农业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等。
(1)绿色农业扶贫。很多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绿色资源,为发展绿色农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葛宏、吴宝晶和欧阳放,2001)。但是自古以来,由于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各自为政的分散经营模式是贫困地区极为普遍的生产方式,这种粗放型经营模式并不利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欠佳、规模较小。因此,国家设立了一系列农业生产优惠政策,如农业补贴、粮食种植补贴、免交农业税等,并主动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指导,从而增强绿色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农业绿色生产为贫困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贫困地区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从而可帮助他们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莫光辉,2016;雷明,2017)。
(2)金融扶贫。贫困居民通常没有正式的就业单位,没有固定的收入,几乎没有储蓄。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贫困居民需要的贷款规模小且不确定,并且贷款需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他们通常希望贷款方式简单、快速、灵活(兰桂华和吴树华,2007)。在金融扶贫中比较典型的扶贫方式为小额信贷,小额信贷自1970年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流行,并成为农户贷款的一种主流的金融扶贫方式。经过4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如泰国BAAC模式、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nit)模式以及“乡村银行”(GB)模式等多种方式。在实践中,许多国家通过小额信贷办法解决了贫困户融资难的问题(Imai,Gaiha and Thapa et al.,2012;Akudugu,2012;Mamun,Mazumder and Malarvizhi,2014;苏静,2015)。胡宗义和罗柳丹(2016)分析了金融对反贫困的作用,发现小额信贷是有效缓解农户贫困的一种方式。此外,吕勇斌和赵培培(2014)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农村金融规模扩大有利于减缓贫困。而鲁钊阳(2016)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出结论,在不同的分位点下,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存在差异。
(3)旅游扶贫。旅游扶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反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就业门槛低、产业关联性强、投资少、见效快等特点。近年来,旅游扶贫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如中国学者赵磊(2011)发现旅游业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加。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旅游目的地的地理区位、知名度、旅游设施等存在差异,旅游业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Thomas,2014)。旅游业发展能够给贫困人口带来短期收益,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旅游扶贫效果更加显著(Sharpley and Naidoo,2010;Croes,2014)。
3.人力资本积累式扶贫
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是中国反贫困过程中两种常见的扶贫方式,救济式扶贫具有时间短、效果直接的优点;而开发式扶贫具有扶贫面积广、辐射范围大的优点。不过两者的缺点也非常突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因此寻求持续有效的脱贫方式非常紧迫。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通常以实物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物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物投资难以奏效,这时需要重点发挥人力资本投资的推动作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必定会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缺乏已经成为贫困居民摆脱贫困的主要障碍(丛立丽和李新然,2008)。众多反贫困实践表明,低素质的人力是农村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最大阻力。因此,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变“输血”为“造血”,是农村地区反贫困的根本(宋本江,2009)。而张友琴和肖日葵(2008)还特别指出,发展教育是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最为关键的实践路径,而且对社会、家庭整体福利水平也有很大的帮助。因而,教育投资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而言,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可以看作推动当今社会发展的“金钥匙”;与此同时,教育投资也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提升人力资本关键在于教育。
综合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式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方式,同样是“造血”式扶贫方式,但是人力资本积累式扶贫区别于开发式扶贫。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式扶贫往往通过贫困人口自身的内部力量,提升贫困人口自身的素质、能力等人力资本,从而增强他们的“造血”功能,进而使之摆脱贫困。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式扶贫实质上是一种“内部造血式”反贫困方式(陈标平和胡传明,2009)。
(四)教育对贫困的影响
教育对贫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Cremina,2012;李锐和赵茂林,2006;王嘉毅、封清云和张金,2016)。理论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教育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教育能够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进而起到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水平和消除贫困的作用(Schultz,1960,1961)。但是在学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认为教育加深了贫困或者教育对贫困没有影响(Bonal,2007)。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Brown and Park,2002;Grace,2010;Rolleston,2011;Tarabini and Jacovkis,2012;Zhang,2014;李晓嘉,2015;柳建平和刘卫兵,2017),下面我们主要从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层次、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法》实施和高校扩招政策实施等方面对教育贫困的影响进行归纳和总结。
1.受教育水平对贫困的影响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受教育水平与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如Mankiw、Romer和Weil(1992)认为正式教育是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并且能够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产出效率。Tilak(2007)以印度为例,在研究不同受教育水平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受过教育的家庭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贫困发生率存在明显差异,且前者的明显要低于后者的。后来,Raffo、Dyson和Gunter等(2009)则进一步例证了受教育水平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学者对此也展开了一些研究,如刘纯阳(2005)以湖南西部贫困县为例,基于农民增收视角,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民收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降低农村贫困程度。刘修岩、章元和贺小海(2007)采用上海市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两阶段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教育与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有助于农户摆脱贫困,且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杨国涛、东梅和张会萍(2010)以宁夏西海固720个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表明农户受教育水平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受教育水平对农户贫困的影响难以判断。杜凤莲和孙婧芳(2011)基于CHNS数据,在研究贫困的影响因素时发现,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等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且户主受教育水平与贫困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李晓嘉(2015)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基于CFPS数据,研究发现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而且进一步发现,延长受教育年限对绝对贫困群体的工作收入影响甚微,但延长受教育年限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工作收入的影响非常明显,不过两者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同时,她还指出受教育水平低下是阻碍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高艳云和王曦暻(2016)以CFPS数据为例,研究了教育改善贫困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而且在多维贫困中,教育的边际减贫效果更大。此外,樊士德和江克忠(2016)、刘一伟和汪润泉(2017)也同样发现受教育水平与贫困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且这一关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脱贫。
也有学者从收入视角出发展开研究,如朱农(2003)采用修正后的Probit模型,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也越高。李春玲(2003)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类似结论,并且还发现教育收益率在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就业人员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农村就业人员。还有学者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受教育水平对居民代际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阻止居民代际贫困传递(卢盛峰和潘星宇,2016;郭熙保和周强,2017)。
众多的学者从增收的视角研究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如白菊红和袁飞(2003)以河南省1000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正向关系,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收入上升。王春超(2004)则以湖北3300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劳均受教育水平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收入上升。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受教育水平对贫困的影响不明显,甚至无影响。例如,中国学者谭燕芝、张子豪和眭张媛(2017)采用CFPS数据,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水平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2.受教育层次对贫困的影响
综合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受教育层次对贫困的影响,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研究不同受教育层次的教育回报率(Frazis,2002;Zhang,Zhao and Park et al.,2005;Kimenyi,Mwabu and Manda,2006;陈晓宇和闵维方,1998;李实和丁赛,2003;范静波,2011;李晓嘉,2015;周强和张全红,2017);研究不同受教育层次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宋玉兰、张梦醒和范宏民等,2017);研究不同受教育层次对就业的影响(刘万霞,2013);研究不同受教育层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叶茂林、郑晓齐和王斌,2003;杭永宝,2007;陈晋玲,2013;张凡、骆永民和方大春等,2016)。
也有不少学者借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直接探析不同受教育层次对贫困的影响。如章元、万广华和史清华(2013)采用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数据,以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山西等五个省市1995~2003年的1832个面板农户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对贫困进行分解之后,借助截尾分位数模型,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层次变量、高中及以上层次变量与暂时性贫困、慢性贫困以及总体贫困之间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高中及以上层次变量的减贫效应要明显高于初中层次变量。张莉(2015)基于青海、内蒙古、广西、陕西、云南、重庆6个省区市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受教育层次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层次的差异导致减贫效果截然不同。总体而言,不同受教育层次劳动者比重的提高所对应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具体来说,除高中以外,小学、初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层次劳动者比重提高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贫困深度,对于FGT总体贫困指数而言,不同受教育层次劳动者比重均与它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也有学者从老年人的多维贫困视角出发,研究了不同受教育层次对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解垩,2015,2017)。
此外,郭熙保和周强(2016)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为研究样本,采用2000~2011年CHNS数据,研究了长期多维贫困的致贫因素。研究发现,家庭户主的受教育层次越高,该家庭陷入长期多维贫困的概率就越低。柳建平和刘卫兵(2017)以甘肃14个贫困村农户调查数据为例,借助Logit模型考察了不同受教育层次对农户收入和贫困的影响,结果认为各级受教育层次均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文盲相比,具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和大专及以上文化受教育层次的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均较低,尤其是高中受教育层次的减贫效果最佳。因此,在西部地区,将居民的受教育层次提高到高中层次会对减贫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而杨娟、赖德胜和邱牧远(2015)则通过构建一个四期的世代交迭模型,分析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认为教育投资水平低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从而促使收入差距扩大、代际收入流动性低、贫困得不到缓解。因此,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不同受教育层次的父代对代际贫困传递存在较大影响(李长健和胡月明,2017)。
3.职业教育对贫困的影响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贫困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OECD研究报告表明,职业教育能够为战胜贫困带来广泛益处,同时也可以为劳动者实现终身学习打下基础,从而增加收入并减少缓贫困(王大江、孙雯雯和闫志利,2016)。近年来,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和地位在学术界和政界均引起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特征、模式、责任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策略等,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不过这些研究大多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如陆小华(1998)较早地提出要重点发挥职业教育的反贫困效能,并且指出在发展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应该有所创新,应该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在实践中探讨挖掘新的施教方式,完善职业教育的反贫困模式。朱容皋(2009)则分析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动力和作用途径以及责任问题。王大超和袁晖光(2012)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贫困地区应该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并且职业教育的对象要以贫困群体为主,目标是提高贫困群体的技能,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制定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王国光(2016)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一条重要途径,并且以尼日利亚为例,分析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许锋华和盘彦镟(2017)以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为例,重点分析了如何构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定向培养模式,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保障。廉僖(2017)分析了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研究现状,并且对此进行了反思。章元、万广华和史清华(2013),程名望、Jin Yanhong和盖庆恩等(2014)则从定量角度对职业教育的减贫效果进行了探讨。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教育回报率角度出发,比较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回报率问题(Neuman and Ziderman,1991;Hollenbeck,1993;Moenjak and Worswick,2003;Meer,2007;Kahyarara and Teal,2008)。Pema和Mehay(2012)、Popescu和Roman(2018)则直接研究了职业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对职业教育与收入或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晚。例如,王海港、黄少安和李琴等(2009),周亚虹、许玲丽和夏正青(2010),颜敏(2012),陈伟和乌尼日其其格(2016)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职业教育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
4.《义务教育法》实施和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对贫困的影响
有关《义务教育法》实施对减贫影响的直接文献相对罕见。从国内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重点探讨了《义务教育法》实施对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如王广慧和张世伟(2009)研究发现,受《义务教育法》的影响,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增量存在明显差异,《义务教育法》实施后,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分别增加约0.8年和1.6~1.9年。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6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年上升至2013年的9.3年。也有学者从制度角度出发,研究《义务教育法》实施的经济效应。根据制度贫困理论可知,制度是否完善是影响贫困状况的重要因素,而《义务教育法》是中国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制度。因此,近年来,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这一政策制度因素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并展开了相应的实证考察。例如,刘生龙、周绍杰和胡鞍钢(2016)以《义务教育法》为例得到类似的结论。国外学者中Piopiunik(2014)从教育传递视角出发,发现联邦德国在1946年和1969年实施义务教育改革后,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义务教育法》实施对个体健康的影响(李振宇和张昭,2017)。虽然这些研究不能直接反映《义务教育法》实施对减贫的影响,但可以从侧面反映《义务教育法》实施与减贫之间存在联系,这也为我们后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呈现快速增加趋势(张先锋、李燕云和刘有璐,2017;马磊和魏天保,2017)。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高校扩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扩招与教育机会均等化方面,即有高校扩招政策后,更多学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这能否缓解教育公平问题,学者们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Blanden和Machin(2013)对英国实施教育扩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教育扩张使得更多富有家庭子女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反在贫苦家庭中这种机会则相对较少,从而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贫富家庭中分布不均衡。但也有学者得到相反结论,教育扩张使教育不平等问题在不同群体之间得到缓解(王伟宜,2013)。后来,张兆曙和陈奇(2013)也同样研究发现,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农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劣势问题得到缓和。甚至还有学者认为,高校扩招后,教育投资差异导致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得到缓解(邢春冰,2013)。此外,马磊和魏天保(2017)通过采用CGSS数据,研究了高校扩招后大学学历溢价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2003~2013年,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要比只有高中学历的劳动者高出32.4%~98.8%。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做了类似分析(Pfeffer,2008;Ballarino,Bernardi and Requena et al.,2008;Polat,2017)。
5.教育发展其他方面对贫困的影响
除了以上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层次、职业教育以及《义务教育法》实施和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外,学者们还从教育发展的其他视角展开了不少研究。
(1)从教育投资视角出发,研究教育投资对贫困的影响,并认为教育具有代际传递性(Castelló-Climent and Doménech,2008;Doorn,Pop and Wolbers,2011;Riphahn and Trübswetter,2013)。如Barham、Boadway和Marchand等(1995)研究发现在信贷约束下,由于缺乏资金,贫困家庭的子女无法受到足够的教育。还有学者认为父代的受教育水平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Aldaz-Carroll and Morán,2001;Christiaensen and Alderman,2004)。Fang、Zhang和Fan(2002)借助OLS回归模型发现,在中国政府的各项公共投资中,教育投资的减贫效果最佳。但Wedgwood(2007)通过采用坦桑尼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投资对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投资并未对消除贫困起到明显的作用。Gustafsson和Shi(2004)通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中国教育支出占比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农村贫困程度也在不断下降;而单德朋(2012)的研究结果却是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不明显。关爱萍和李静宜(2017)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1408户农户,研究发现以教育投资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户家庭贫困程度,教育投资越多,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邹薇和张芬(2006)通过扩展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教育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减缓贫困。
(2)研究教育公平对贫困的影响。如杨俊和黄潇(2010)通过CHNS数据发现,缩小教育差距,有利于贫困的减缓。受教育机会也是教育公平的表现,因此,有学者从受教育机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如周强和张全红(2017)根据2000~2011年CHNS数据,以社区(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数量作为衡量受教育机会的代理变量,研究了受教育机会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各级受教育机会对家庭贫困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不同层级的受教育机会对家庭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而这一影响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同样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也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和代际职业流动视角出发,分析居民接受教育机会对贫困的影响,研究也表明受教育机会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进而影响居民职业流动状况,人力资本积累越高,居民流入高收入阶层的可能性越大(卢盛峰、陈思霞和张东杰,2015)。
(3)研究教育质量对贫困的影响。单德朋(2012)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西部地区2000~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例,研究发现教育质量与城市贫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且教育质量的减贫效果比受教育水平更为显著。王玺玮(2017)以湖北省13个市州面板数据为例,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并且两者结果相似,教育质量的提升能够缓解贫困。
(4)教育致贫的相关研究。教育致贫论者认为提高受教育程度反而会加大贫困程度。“因教致贫”的概念于2004年由“新华视点”正式提出。随后,在学术界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其中,彭兴庭(2005)认为教育导致农村家庭贫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杨小敏(2007)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借助经济学预算线分析了教育致贫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教育致贫的具体原因,从而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教育致贫问题的对策建议。随后,曹海娟(2010)也分析了导致教育致贫的各种可能因素,并探析了教育致贫问题发生的机理。而毛伟、李超和居占杰等(2014)基于人力资本、亲贫困增长等理论,通过构建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研究发现教育数量显著恶化了贫困状态。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教育致贫的现象并不是发生在每个教育阶段,主要是发生在高中以上教育阶段(文宏和谭学兰,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