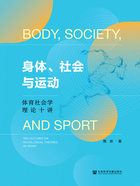
二 社会学视域下的体育——从身体活动到文化实践
(一)体育概念的社会学之争
在西方学术界,学者们普遍认为“体育运动(sport)是一种制度化的、竞争性的、以一定身体运动技能为基础的、以个人享受或得到一定回报为动机的活动”[2]。这个概念界定也主要从身体和心理的层次来理解体育。对于这个定义,也存在一些质疑。比如有人就提出:根据这个定义,下象棋是不是体育?因为下象棋并不是以身体运动为基础的。两个小孩相互追逐算不算体育?因为这项活动一定不是被制度化、有规则的活动。几个人在一起跳健身操,这种没有竞争的身体运动算不算体育运动?因而这种看似完善的定义并不能涵盖人们常识中的体育运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看到体育的目的和内容都大大超出了原来的范畴,体育的概念也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在中文语境中,当用于广义时,一般是指体育运动,其中包括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当用于狭义时,一般是指身体教育(PE)。[3]在英文的背景下,“sport”主要指的是具有一定制度性(有规则)的体育竞赛;而“physical exercises”或“fitness exercises”主要指的是身体锻炼;“physical education”是指体育教育;“games”一般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竞赛活动;“sports activities”主要是指以竞技为核心的一般体育活动或者训练。在体育生理和医学界,常常用到“physical activities”即体力活动,这个概念更广泛,不仅包括以娱乐身心为主的体育活动或者体育锻炼,还包括劳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身体活动。这些分类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体育认识的变迁过程:从自然的身体运动到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因此体育研究也逐渐从教育学、科学、医学进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领域。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体育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体育和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外在、内在关系?人和人又是怎样在体育的方式下产生关系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体育带给人们什么,人们又是怎样改变体育的?总之,人们不仅想了解围绕体育所发生的社会现象,更想探究这些体育现象下更深层次的意义。人们不断地意识到体育不仅是个人的身体活动,而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了解体育,需要从与体育相关的各个社会方面去讨论。与此同时,通过对体育的研究,人们进而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更加了解。
(二)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活动
sport这个词最早起源于法语的desport,意思就是休闲。而在英语中最早的关于sport的定义是一种娱乐,除此之外还有赌博、狩猎、游戏等需要以身体为媒介所进行的活动。波斯人认为sport是一种赢得胜利的活动。而现代希腊人对sport的理解,则强调其为塑造健壮体格的身体运动。从中国的文化背景来看,体育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军队的训练;另一种是为了自身或大众的娱乐。无论是身体的训练还是身体的娱乐,体育在人们的观念中一直就是一种围绕身体的运动。这种观念持续影响着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作为人类的肢体承载和行为的外化实体,身体确实是体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20世纪前期,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关于“体育是以大肌肉活动为方式的教育”的观点盛行一时。这个观点给人们两个启示:第一,体育是一种教育手段;第二,体育是大肌肉活动或以大肌肉活动为主的身体活动。我们暂且不评判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它确实能代表一大批学者对体育最基本的认识。
其实,西方思想界从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对体育有一定的阐述,而这些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观点都是围绕着身体-心灵教育这一主线的论述。这一时期,首先,人们开始抛弃精神领导身体的观点,意识到灵肉一致,因此体育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其次,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重新得到重视;最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身体成长与教育的关系,体育开始把教育与医学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
1762年,卢梭(Rousseau)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儿》(Émile,ou de l’éducation)一书。他使用“体育”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儿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卢梭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自然教育论”之中。而自然教育论也是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石。自然教育论的核心是强调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所谓教育,干涉或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他的自然教育有三个来源:自然、周围的人及外界事物。卢梭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健康、强健的身体是儿童智育和德育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感觉器官(身体)是儿童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儿童通过各种感官积累丰富的感觉经验,为他们在下一阶段发展智力和判断力打下基础。因此,他特别强调感官的训练,尤其是对身体素质的训练。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各种感官的训练方法。例如,他主张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锻炼触觉,通过画图、认识集合图形来训练视觉和观察能力,借助听歌曲和音乐来发展听觉,等等。卢梭认为教育“或受之于自然,或受之于人,或受之于物”。他认为,(1)人类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2)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3)我们通过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在这三种教育中,只有人的教育是我们能真正加以控制的,它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在这种教育中,对身体的教育即体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卢梭认为体育可以增强人的智力,这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要培养儿童的智力,应当先培养智力所需要的体力,“为了使儿童敏慧,你要给他的身体不断地锻炼,使他的身体强壮而健康,你应该让他奔跑、喊叫,让他成为有体力的人”[4]。其次,卢梭认为体育能够培养人的意志,这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对于青少年要训练他们经得起将来有一天必然要遇到的打击,锻炼他们的体格,使他们能忍受饥渴和疲劳,通过体育锻炼来磨炼青少年的意志。最后,体育可以培养人的优良品质,这是卢梭从古代欧洲教育家的体育观点中汲取的养料。他让爱弥儿去亲自观察社会,在体育活动中体察人类的苦难和艰辛,因此,爱弥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尽力去做,而且希望比别人做得更好。赛跑时,脚步要跑得最轻快;角斗时,要比对方强;工作时,技术要比别人巧。这就是在体育中培养的求实精神。
除了卢梭,洛克(Locke)也是早期关注体育教育的思想家。洛克认为应该从体育、德育和智育三个方面培养年轻人。洛克关于体育教育的理论主要体现于《教育漫话》这本书中。洛克在这本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是对于人生幸福的一种简短和充分的描绘”,“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健康是为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福利所必需的,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什么福利、有什么幸福”,“凡是身体和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5]从这些引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洛克指的健康是以身体健康为基础的。在他看来,身体强健的主要标准是能否忍耐劳苦。他认为儿童应该从小就开始锻炼身体,并用自然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他认为室外活动是比室内活动更加有效的教育方式)来进行锻炼,要让他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另外,洛克提出了绅士体育,表达了资产阶级这个新兴阶级在17世纪的教育要求。绅士体育的目的就是通过体育、德育、智育等世俗教育把资产阶级的子女培养成为新贵族——绅士。他主张把绅士体育的内容作为体育手段,教育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才干、善于打理自己事业的绅士。他认为作为一名绅士,必须具备体、德、智“三育”才能实现自己真正的幸福。因此,洛克在体育锻炼和保健卫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科学水平的主张和建议。他提出的锻炼内容包括当时英国上层社会流行的游泳、划船、骑马、击剑、舞蹈和旅行。他还从医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的保健主张,这在禁欲主义仍具有强烈影响力的时代产生了开创性的意义。
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是另一位现代体育教育的启蒙者。西方人认为,他是对顾拜旦奥林匹克思想的产生最具影响力的人。阿诺德在体育方面的功绩在于他通过对英国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的改革,把英国传统的竞技游戏引入学校,初步形成学校体育体系。阿诺德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的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和身体极度疲惫和脆弱,绅士教育的理念也岌岌可危。阿诺德想通过身体教育来改善人们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因此他把体育活动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校广泛推广。英国传统的户外运动(游戏和比赛)本来就在拉格比公学之类的私立学校占有重要地位,最风行的是板球、橄榄球、划船和狩猎。阿诺德利用学生自治管理,使这类运动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竞赛活动(games)。1839年10月,阿代莱德女王访问拉格比公学,对其体育大加赞扬。此后其他学校竞相仿效,从而使有组织的体育竞赛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随着英国的对外发展,“阿诺德方式”传到世界各地,对世界竞技运动产生了强烈影响。近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到英国旅行时,很赞赏英国学校的体育竞赛,后来他在法国的学校中也开始积极推广。这时候的体育渐渐开始脱离个人的身体锻炼,而逐步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体育意义的理解也主要集中在体育对人类身体-精神的功能上。
17~18世纪,人们主要从教育角度去认识体育,确立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奠定了体育教学的组织、手段、教材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基础。19世纪,近代实验科学开始成为探索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有力工具。德国人菲特(Gerhard Vieth)于1794~1975年出版的《体育百科全书》,第一卷是体育史,第二卷是体育科学,他在解剖学、生理学基础上对身体运动进行分类,并用数学、物理学加以解释,这两个方面都是首创。德国人施雷贝尔(Schreber)于1855年出版《室内医疗体操》。法国人布洛卡(Broca)1861年创造多种人体测量仪器,在此基础上,1870年,比利时人格特勒(Quetelet)出版《人体测量学》。这些著作奠定了体育科学的基础,但同时也限制了体育研究的视野。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体育教育学(Physical Education)和医学占据了体育研究的主要领域,体育也作为一种自然科学而被讨论和研究。这反映了体育研究仍以“身体活动”为核心思想。
(三)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系统
从早期人们对体育的关注来看,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道德方面,学者们大多把体育运动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人的身体活动上。体育科学的形成也体现在以近代医学和教育学为基础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直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陆续有学者把观察体育的视角从身体转移到了社会,这打开了体育研究的另一扇大门。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于1767年首次提出体育运动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6]既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就会有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他观察到体育是一种集体仪式,它对社区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弗格森对体育的理解第一次把体育的概念从身体、心理层面延展到了社会层面。他看到了体育的社会意义。继他之后,体育的定义不断被发展。约翰·洛伊(John Loy)1968年在《体育的本质:对定义的尝试》一文中递进式地对体育进行了定义。[7]
第一,体育是一种实际(actual)的游戏(play)和特殊的事件。“实际”强调了体育是客观存在和真实发生的,“游戏”强调了体育不是单纯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ies),而是具有一定互动性、规则性的活动,这与个体的身体锻炼进行了区分。
第二,体育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play),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游戏(games,竞赛)。这意味着,体育这种游戏不是临时的、偶发的、片段的,而是被(成文或不成文)“规定”下来,并且按照共同制定的程序、规范定期地进行,且具有持续性和普适性。
第三,体育进而是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即体育不仅是游戏(活动、事件)本身,还包含制定规则、运行比赛的团体、组织和机构。
第四,体育还是一种社会情形(social situation),即体育也包含其发生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环境,同时也折射出参与者所处阶层、性别、种族等社会结构。
第五,洛伊启用了斯梅尔塞(Smelser)的观点,认为体育是一个抽象的整体(abstract entities),它把不同模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到特定的价值观、知识、习俗、认可以及社会情境中,并制度化为某一项体育运动。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足球运动时,我们想到的不仅是踢足球这个具体活动,还会想到世界杯、欧冠赛,想到国际足联、皇家马德里,想到马拉多纳、梅西、贝克汉姆,想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
综上,根据洛伊的定义,体育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即体育秩序是由一定社会团体组织、规定和支持的人类活动,又是一种社会情形,即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背景。虽然体育参与会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情形,但洛伊认为这些社会情形大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社会系统是指一组特定的人(部门)以及这些人(部门)之间通过互动建立起来的关系。[8]将体育看作一种社会系统,为体育成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也激励了学者们从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究体育活动,分析人类进行体育活动的动因、参与的程度以及体育活动对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
(四)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
除了以上两个概念以外,还有社会学家认为体育就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即文化[9]。与系统视角多强调客观关系不同,把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强调了体育的主体——人的能动性。就像其他文化实践现象一样,体育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和其生活紧密联系的文明的创造。[10]也就是说,体育不仅是在个人和集体历史之外形成的现实事物(actual play),还是人类实践的结果(being created)。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理解为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物质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11]把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去阐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楚体育的本质。
第一,体育的客观现实性,即体育是人的客观物质活动,具有客观现实性。体育实践是一种能够使外部对象(社会文化)发生某种改变的现实的物质活动;体育实践的结果是现实的(如获得胜利、身体健康),但是实践的水平、广度和深度都受客观条件(如经济、政治、教育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如生命周期规律、训练规律)的支配。
第二,体育的自觉能动性,即体育是在一定思想、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不是消极适应环境,也不是本能活动(如条件反射的行为),而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如为了娱乐、健康、社交)。体育实践不仅能使对象(比如体育规则、运动的方式)按照人的意图和需要发生变化,同时还会主动去认识体育的本质和规律(如体育科学研究),充分体现出人的自觉能动性。
第三,体育具有社会历史性,即体育会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体育实践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凭借和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所进行的现实的社会活动,因此其内容、性质、范围、水平等都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体育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而并非一种固定的活动和一成不变的事实(social facts)。
总之,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的高级文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具有独立体系的文化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它折射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着社会发展的轨迹。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的渗透,西方体育界开始关注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12]他们或运用历史分析或实证的研究方法,或通过文化解释的途径来揭示体育与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关系,并深入思考体育现象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