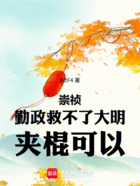
第61章 鸿门宴
吴襄小心翼翼回道:
“已经进城了。”
袁崇焕点点头:
“你下去吧,告诉毛都督好好休息,晚上本督在宁远城内设酒宴为他接风洗尘。”
吴襄应诺一声起身离去。
等帐内只剩下自己,袁崇焕镇定自若的表情很快阴沉下来。
他一伸手,从官服蟒袍的暗袋中掏出已经反复观看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奏疏——
自从八月底,他已经三次上疏天子,催讨八十万两欠饷,要求撤销辽东巡抚、登莱巡抚两个职位。
天子的回复和以前一样迅速,
然而朱批内容却从半个月前的“准奏”,“依卿所议”,变成了三次全都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知矣”
说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夸张——三次天子的朱批都是用同一颗印章印上去的。
“知矣”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亲笔批复,只用印章,又是什么意思?
袁崇焕百思不得其解,天子在平台召对后明明对他信任有加,口称要将辽事尽托于自己一人。
之后也确实说到做到,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为什么只过去了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因为焦虑,袁崇焕已经一个星期睡不好觉,前天实在忍不住给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写了一封信,委婉询问最近京城出了什么变故。
只是这种私信无法用八百里加急,换马不换人的方法传送,估计现在还没有到钱阁部手中……
到底是谁在给自己使绊子,在天子面前进了谗言?
满桂当然是最大嫌疑人,这莽夫在宁远大捷就不听袁崇焕指挥,战后被参了一本,不予请功,肯定是记恨上自己了。
但是满桂一个武将,又没有密奏的权限,
常规奏报奏疏需由兵部转呈——袁崇焕自己现在就是兵部尚书,满桂要是有什么小动作,奏疏在他这里就被截下来了,绝对送不到通政司,更遑论惊动天子了。
满桂之外,自然是满桂的保护伞,袁崇焕的前上司辽东督师王之臣了。
王之臣身为文臣却包庇满桂一个武夫,还没有容人之量,用不了袁崇焕这样真正有才能的人,几次冲突甚至逼得袁崇焕和他一起打辞职报告。
这老头三甲进士出身,为官三十余年从知县一路做到督师,
在朝中甚有人脉,确实有能力直接把小报告打到皇帝面前。
不过袁崇焕早就预判到王之臣可能的威胁,早在七月底平台召对时,已经先向崇祯告过王之臣的黑状。
以当时天子的反应来看,显然已经给王之臣记上一笔。
所谓先入为主,王老头哪怕有能力密奏,也不至于能影响到皇帝的看法。
有一个人绝对有能力影响到天子对袁崇焕的看法——
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
袁崇焕任宁前道时,曾经擅自诛杀过一个姓杜的副总兵,引得孙老头勃然大怒,当众劈头盖脸骂他没有尚方宝剑,不提前上奏便乱杀边将,是“专杀”。
这次进京平台奏对给天子画的“五年复辽”大饼,也与孙公去职之前反复强调“稳扎稳打”的战略背道而驰。
如果换个人,因此怒向胆边生参上一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
袁崇焕对孙老头的节操还是心里有数的——自己这老师唯一的缺点就是心软,决计干不出背后捅刀子的事情来。
所以,
既有能力,又有动机,还没节操。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选了。
袁崇焕起身背手走到屏风上的地图前,目光停留在最东侧几个已经画上红色圆圈的孤岛之上。
东江镇,
毛文龙!
论动机,袁崇焕和毛文龙互相看不顺眼,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论能力,毛文龙任左都督,节制东江镇,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这次上任蓟辽督师,袁崇焕早就已经做好打算,自己立威第一个要下手除掉的就是毛文龙。
但是反复权衡为大局考虑,最终还是决定先通过粮饷拿捏毛文龙一番逼他低头,
等明年自己亲自去东江镇再动手,免得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内讧起来失去一个建虏后方的重要牵制点。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刺头儿居然胆大包天,恶人先告状,先向皇帝打了袁崇焕的小报告!
既然如此,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反正袁崇焕主意已定,既然自己坐上蓟辽督师的位置,毛文龙的脑袋就别想安稳在肩膀上待到他卸任。
择日不如撞日,就趁这次毛文龙上门来拜会直接杀掉了事。
……
九月初的宁远城,天气转凉,街道上已经时不时能看见几片枯黄落叶随风飘荡。
“卑职东江镇总兵毛文龙,恭请督师钧安!”
袁崇焕看着眼前长揖到地的毛文龙,面上满是和善笑容:
“毛总兵里面请。”
这跋扈之徒,见了自己堂堂蓟辽督师居然不行跪礼!
进到督师府正堂,武将们各自在八仙桌旁入座。
袁崇焕面朝正门,背对九边防务图,在主座上安坐,其下依次是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吴襄等人。
毛文龙则坐在右首,其下依次是东江镇毛承禄、孔有德、耿仲明等主要将领。
酒过三巡,众将皆有了些醉意,
袁崇焕对毛文龙举杯笑道:
“毛总兵,圣上特赐密谕,关乎东江将士封赏,然旨中言明‘止传尔一人’,可否借步后堂?”
说话声音不大,东江镇将领们却仿佛被触碰了什么开关,一齐转过头来,目光如电盯在他身上。
毛文龙义子毛承禄是个大嗓门:
“朝廷封赏有何机密可言?督师为何不当众公示?”
果然一帮骄兵悍将,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竟然敢对整个辽东最高长官这般大呼小叫!
不用袁崇焕自己说话,下手次席祖大寿已经勃然大怒,按住剑柄站起身来看向东江诸将:
“区区匹夫,安敢僭越蓟辽督师钧令?《大明会典》明载‘五军都督府见兵部堂官,行属官礼’,尔等东江镇将,岂不知‘文帅掌印,武臣听调’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