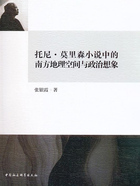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建构:《秀拉》中的身体实践
《秀拉》成书于1974年,是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与《最蓝的眼睛》中受白人价值观摧残的主角佩科拉不同,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来自黑人群体的叛逆女性形象。有评论称,“在某种程度上,秀拉是70年代小说中最激进的角色”[6]。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按年代描写黑人女性建构起主体意识的过程”[7]的书。确如评论所言,《秀拉》展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作品中匹斯家的三代女性无一例外地对女性主体性建构做出了贡献,演绎了一段完全异于“底部”黑人社区其他黑人女性的生活历程。三人抵达女性主体性的方式惊人地一致:以日常身体实践来完成女性自我的建构。在这部作品中,很少出现白人对黑人群体直接的身体戕害,取而代之的是黑人女性主动的自我身体实践。她们通过种种对身体的暴力、放任和粗暴干预而达至某种自在状态。在“底部”,她们面对的是白人对黑人群体的歧视和倾轧、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和塑造等,这些成为“底部”女性生成和发展自我的障碍。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哲学家或派别对此有着不同的阐释。后结构主义流派对主体性的解释基本上跳出了传统认识论对“自我”的本质主义思考,大多数理论家都倾向于把“自我”置于社会中进行考察,认为主体不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或者某种稳定的人的属性,而是一种语言、政治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哲学中,德勒兹的“块茎”概念为其多元哲学提供了一个恰切的视角。在他众多的哲学术语中,“逃逸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勒兹将线分为三种:克分子线、分子线和逃逸线。克分子线是一条界域化的线,有着明确配置;分子线是存在于众多块茎之间的节段性的分割线,它游走于整合和分裂之间;逃逸线是从辖域化中逃逸出去的线,能够在任何时间穿越边界线,它逾越了“它的被解域的符号所特有的指数(indice)”[8]。因此,一条逃逸线可以被理解为达至外界的一种方式,可以创造出已建立的局限的绝对的异质性来,同时具有否定性和创造性的价值。块茎式的网状通过逃逸线肯定了差异(异质性)。逃逸线并非消极的,而是具有生产性和革命性的积极力量。与《宠儿》中对黑人身体的规训有所不同[9],《秀拉》中的身体实践是自发的、积极的,具有德勒兹式的“解域化”特点,小说中的女性通过自己的身体实践构造了不同的“逃逸线”,从而突破了由当地黑人群体的文化传统和日常实践所构筑的同质的、公共的层化空间,最终确立自己鲜明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