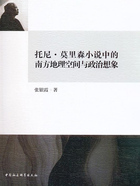
一 界域化空间:梅德林“底部”
德勒兹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提出了“界域”的概念。界域是环境和节奏的某种结域的产物,“它是由环境的不同方面或部分所构成的。它自身包含着一个外部环境,一个内部环境,一个居间环境,以及一个附属环境。它本质上是为‘标识’所标志出的,而这些标识则可以是取自任何环境的组分:质料,有机的生成物,膜或皮肤的状态,能量的来源,感知—行为的简缩形式。确切地说,当环境的组分不再是方向性的,而变成维度性的,当它不再是功能性的,而变成为表达性的,界域就产生了”[10]。概言之,界域其实就是一种标识,自身是由各种质料或运动等不同的配置组成的。
界域尽管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比如一首叠奏曲就是一个界域,但它天然地与空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德勒兹说故乡就是一种界域性表达。故乡,就是先天性和获得性在界域性的配置之中所呈现的新形象。[11]故乡区别于其他空间的地方就在于其特殊的配置,它形成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界域化的空间。比如居于其间的人、具体的地理空间布局、长期生活形成的权力结构和传统等,这些因素在广袤的平滑空间中形成了对个体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线条,它清楚地标示出了某处与其他地域的差别。在小说《秀拉》中,梅德林就是这样一个界域化的空间。对北方甚至更大的区域来说,梅德林是一处平滑空间,是具有游牧性质的存在,而就其中的居民来说,梅德林这个处于俄亥俄州被城市包围的黑人社区又是一个界域化的空间。是什么构成了它的配置?
“底部”(The bottom)标示出鲜明的政治权力结构。“底部”是小说主要的叙事空间,位于俄亥俄州。这个称呼是白人命名的,当年黑人居住时却被叫作“底部”,如今白人称之为“梅德林郊区”。“底部”这个名称源自一个黑人的笑话。镇子里一个好心的白人农场主许诺了他的黑奴在完成一件难办的事情后便给他人身自由和一块低地,黑人按要求完成了事情并向主人索要曾经许诺的土地和自由。白人主人不想给他谷底的低地,就把一块位于山顶的土地给黑奴并解释说这是“天堂的底部”,“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了。那是天堂之底——有着最好的土地”。[12]自此,位于梅德林山顶的地方就被叫作“底部”。“底部”水土流失严重,种子会被冲掉,冬天寒风呼啸,黑人耕种十分艰辛。这个充满了政治讽喻的笑话生动地展示了梅德林的政治权力结构:白人居于统治地位,黑人是政治权力统治的对象,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境地。黑人在“底部”山顶忙于生计,根本无暇欣赏后来被白人认为此处可能真是“天堂之底”的郁郁葱葱的山顶风景。正如评论指出的,“黑人社区死于白人社区的反复无常”[13]。
“底部”是典型的黑人社区,黑人传统文化作为界域的标识和配置,它塑造了此处的人文环境。莫里森曾在一次访谈中谈道:“有成千上万的像梅德林一样的小城,那儿是大部分黑人的聚集地,是黑人的精神源泉,就是在那儿我们建构了自己的身份。”[14]俄亥俄州是南北战争后南部居民最早的迁徙地,包括作家出生的洛兰镇,都是典型的南部移民形成的黑人社区。迁徙居民自身携带着他们曾在南部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有评论指出,黑人居住区伯特姆(即“底部”)“指向过去,那南部乡村,为给现代化开路已像黑刺莓那样被根除的文化的蓄水池”[15]。《秀拉》中梅德林作为黑人社区的突出标识之一是其群居的、封闭的生活。“底部”尽管位于美国最老牌的工业州,但工业化的推进并没有深刻地影响黑人群体的生活。他们与工业化城镇只有一河之隔,但这仅有的路程却将黑人群体隔绝于现代化进程之外。黑人少女奈尔跟随母亲去了一趟弗吉尼亚,自我开始觉醒,尽管她暗下决心要走出这个地方,但儿时的南部之行成了她一生唯一走出梅德林的经历。黑人青年裘德盼望自己能在修路工程中大展身手,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只能像大多数黑人一样从事农业生产及低贱的服务行业。梅德林就像莫里森笔下的沙理玛、埃罗和洛特斯一样,都是“被”封闭的黑人社区,社区内部保持了一种农业社会形态。黑人群体彼此走动,很少和白人有所往来,他们安然地从事耕种生活,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传统。
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是对人们普遍道德感的追求,尤其是族群内部的规约,这是梅德林突出的标识之二。通读小说,除了匹斯家的女性及奈尔和夏德拉克外,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相同的伦理面貌——充满道德感或为传统观念所左右。20世纪初期,美国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爵士时代后,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小说从20年代写到40年代,“底部”社区并没有受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道德观念。“在秀拉把伊娃送进养老院时,那些原本咬牙切齿地抱怨照顾上了年纪的婆婆的女人曾有所改变,开始任劳任怨地刷洗老太太的痰盂。秀拉一死,她们就迅速恢复了对老人所带来的负担的怨恨。妻子们不再悉心照料丈夫,似乎再无必要去助长他们的虚荣。”(166)“那些当年在秀拉的恶意下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现在找不到对手了。紧张气氛烟消云散,她们也就失去了努力的理由。没有了她的冷嘲热讽,对他人的爱也就陷入了无力的破败。”(165)秀拉的特立独行挑战了镇子上的道德观念,她在追求个人主体性的过程中打破了梅德林的传统,被看作是带来厄运的“女巫”。而她也被置于道德制高点的反面,人们因为秀拉的存在而有意回避人性中恶的一面。秀拉的遭遇从反面证实了“底部”的公共伦理,高度的道德观念是镇子在现代化浪潮中得以良性运转的重要方面。
叙事中男性的被阉割揭示出这个黑人社区的日渐萎缩。小说里的男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人物逐渐隐去,包括三个杜威、柏油娃娃以及李子等。唯一表现出强烈主体性的夏德拉克被认为与非洲的水神有着密切的关联。[16]这种男子汉气概缺失的现象缘于白人的涌入和他们对黑人生存空间的挤压。奈尔的丈夫裘德曾对未来充满信心,期待在梅德林的建设事业中大展拳脚,但却屡次被排挤在筑路工人行列之外,“他一连六天排在登记做工的队伍里,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工头挑走来自弗吉尼亚山里来的细胳膊瘦腿的白人男孩、脖子粗壮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一次又一次听到‘今天没活儿啦,明天再来吧’的通知后才明白的道理”(87)。“他们(新涌入的白人)形成了一个地理排斥区”,正如贝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它的作用与其说是将黑人社区住户安置于“底部”,不如说是将其从白人主导的环境中“移除”。[17]愤怒的裘德只能通过与奈尔的迅即婚姻来表达他满腔的男子汉气概。在梅德林这个混居的环境中,黑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渐趋萎缩,广大黑人群体渐渐成为一种“缺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