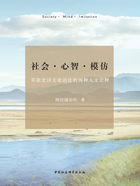
第三节 从内容到形式:作为文化语法的诗学
草原史诗的诗学构建(《蒙古族诗歌美学论纲》[58]和《史诗的诗学》),聚焦于诗论范畴的宏观维度和系统化的理论总结,关涉蒙古史诗传统的本体诗学、诗性范畴和本土解读三组问题。这些不仅是整个蒙古史诗诗论的最基础部分,同时也是诗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沿着以上的思路,可把史诗诗学语法构架分为三大版块:以思维特征和审美结构为中心的本体模式(特征论、宇宙论和形象论),以艺术史视野和关系结构论为基准的形态模式(形态的发展论和艺术自然论),以民族诗学的智识谱系为经验基础的本土模式(民族诗律论)。其中,本体诗论和本土批评的结合研究是以上三大批评模式的核心联结,也是诗学批评论的主要增长点。以上三种模式的总和基础是审美形态批评,因为其有机地融合了社会伦理和历史批评的两种维度,从而标定了诗学批评的审美基础和本位范畴。
史诗诗学的本体特征论。该视域从诗性的本质入手,以思维特征和心理结构的结合分析为准线,发掘其社会伦理和道德范畴的本体维度,建立在以诗性观念的本土特性为前提或依据的宏观基础上。史诗诗学把史诗看作文学的诗性样式之一,认为史诗不仅是关于蒙古族生存情形的“百科全书”,更是蒙古族语言艺术的“经典模型”。史诗文类是文化思维范畴的审美结构之直观映射,而语言和历史、信仰和宗教、哲学和民俗等多重结构的文化语境则是史诗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因此,史诗文类的审美基础映照出文学的或艺术的本体论维度,而史诗的综合范畴则展示其多维结构的复杂特征。
史诗诗学的本体宇宙论。该论域着眼于本体的哲理范畴,以心理学或思维模式的分层论解析为中心,挖掘其空间、时间和数量范畴的本土维度,因为最根本的准线是以生命本体观的层次论和分类框架为基础的。史诗诗学指出,在史诗世界里,时间、空间和数量三个概念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四维(空间的三维和时间的一维)的时空观念。例如,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历时上的神——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空间上——上、中、下,等等;这些都是与神话传统和人类原始思维息息相关的普遍性话题,尤其与极具古代神话思维特征的数字“三”等有着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从艺术化的空间说,关于“地理”的描绘与蒙古英雄史诗的经典形态和“历史虚构”有着内在的关联,其地理的称谓更是作为诗性地理之名称,而很难被理解为具体地理之名称。此外,从史诗方位的分类特征看,它的基本趋势也与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和蒙古民众的原始思维、原始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数字的体系往往与神话思维、习惯风俗、吉祥象征相关联,成为本土智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还与时空认知体系连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民族文化本土智识的完整体系。
史诗诗学的本体形象论。该分域紧扣本土的观念范畴,以心理学或思维模式的二元论分析为根基,观测其心理学前提或思维结构基础的本土维度,进而勾勒以本土观念为基础的结构论和分类学模式。譬如,正反面的黑白体形象系以二元结构的本土观念模式为基准,各自形成了关于美的形象诗学和有关丑的形象诗学,并为诗学形象论的开启提供了观念基础和批评张力。即,以好与坏、美与丑、正与反、生与死、吉与凶、正义与邪恶(悖谬)为准线的分类学基础,作为风俗和审美感的总趋势,源自蒙古民众对黑白分类的古老认识或观念模式;其中关于类型化和丑审美的诗学问题的看法是整个形象批评论的关键突破口。史诗诗学认为,“蟒古斯”形象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代表,保留了人类与野兽的某些特性,是重合社会与自然之特性的,结合现实与幻想的容量大的“复合形象”。作为白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它具有“反审美的价值”,以反面形象充实并填补了审美价值的体系构架。驴子形象作为骏马形象的鲜明对比,与蟒古斯形象一样不仅具有“反审美价值”,并且它们之间又形成了正比的价值关系。丑的诗学批评范畴,包括“愚蠢”人物的怪异形象论、恶魔蟒古斯的形象论以及坐骑驴子的形象论,等等。这些均与蒙古本土文化的民间性和人文伦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还与正面形象的“美”的诗学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蒙古史诗形象诗学的整个体系和结构基础。
史诗诗学的形态发展论。该视域从艺术自身的内部规律出发,以不同时期的演化轨迹和形态特征为中心,摸索其社会历史的多重维度,并阐明了社会历史和艺术发展观之间的对应关系。正如史诗诗学所指出,整个蒙古史诗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原始史诗、成熟史诗和变异史诗;演化轨迹正反映了蒙古史诗传统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和历史变迁,后者包括受萨满教、佛教和农业文化影响的变化等。其一,艺术自然的形态批评以审美世界的三重化结构为中心,揭示了形态批评的结构关系论和本土审美之多元维度。就其本质而言,艺术自然论既属于本体批评的范畴,又属于形态批评的范畴;前者的依据是审美结构和思维特征研究的本体基础,而后者的根据则是以结构化的层次为中心的关系论基础。因为,史诗的艺术自然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理想化的自然、人格化的自然和超自然;分类学依据是以和谐、比拟和夸张为主线的三种诗论概念,而更大的关系论基础是宗教信仰、审美范畴和价值效用。其二,诗律论的批评以意象、韵律、风格三个诗性概念的分析论为重点,并从微观和宏观视角相结合的角度展示了其民族诗论的内部规律和民间智识的生成原理。从地方性智识的美学传统看,“力”“度”“色”是构筑蒙古乃至草原史诗崇高风格的三个基本要素,观念基础均来源于本土智识的审美体系。相比之下,关于意象和韵律的批评模式以本土诗性智识体系的宏观本体分析论为基石,而风格的批评模式则以本土诗性智识体系的宏观综合论为基础。很显然,形态发展论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和文艺学的本体论方法为基础,而且这种立足于具体历史、社会分析、人种学及美学等多维视角,并对其诗歌的历史轨迹进行探究是蒙古族诗学理论,尤其是草原史诗诗论的综合前提和宏观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