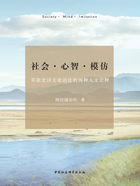
第四节 口传文化语法:社会行动·文化心智之模仿
本书着眼于社会行动·文化心智及其模仿论视角,回应了史诗学即口传民俗学领域的表现·反映说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拟剧理论(尤其是维克多·特纳和欧文·戈夫曼)等主观化假设的错位问题,并从理论假说案例和类型逻辑的模仿(本体)说的深度结合角度出发,力图阐明表现·反映说和社会拟剧论对其本体假设的误差判断与偏差理解。也就是说,书中视草原史诗的类型学和诗学(包括诗歌美学)两大方向为民俗文化语法探索的成功典范,并把20世纪后半期涌现出的这两大史诗研究主题并置于学术史的整体化语境中加以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勾勒出其各自形成的思想来源和方法论基础、术语体系、批评模式等和与此相关的表现·反映说之偏差认识概貌,还回应了社会拟剧论的错位假定问题。当然,主要理论依据来自引言部分的相关解说。
第一章以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思路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大型口传民俗即史诗传统的文化语法研究进路——类型学和诗学的两大课题。认为,这不仅是草原史诗学所有理论性探索的根本基础,更是深入挖掘以史诗的类型学和诗学为中心的口传民俗文化语法问题——社会行动·文化心智模仿原理的核心所在。从草原史诗研究的学术历史看,以上两大论题各有其思想和方法论的源头,也有其各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特定规律。
第二章追溯并考察了史诗的类型学和诗学两大研究路径的思想来源和方法论基础。第一节是史诗类型学方法的考察:从原型论与文化史的视野入手,剖析了其关于历史主义和类型学两个维度的学理性思考和实践,并就居于中心地位的发生学、还原论和类型发展论等进行了深入解读。第二节是史诗诗学的考察:从本体论与艺术史的视野出发,分析其美学、哲学和诗学三维理论走向的渊源及演进历程,进而讨论了本体诗学、元范畴和本土解读三个向度的问题。
第三章把草原史诗的类型学看作社会行动模仿的文化语法范型,解析了其方法论模式和范畴基础等构建论题,并在三个层面上分别展开:发生学前提、类型学还原论和发展论模型。第一节分析了以前提论或目的论为主线的发生学课题,核心是时间范畴的历时源头和空间范畴的发源地。第二节论析了以还原法为基石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包括艺术本源的复原和社会原型的还原两个版块。第三节进入类型的发展论课题,重点在于以类型和发展为主的形象研究和情节结构论两方面。第四节试图论证社会行动模仿的类型学及语法框架特征,其以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民俗学理论,在共时和历时的时空维度上勾勒整个蒙古史诗传统的产生、发展及成型过程为考察点。
第四章将草原史诗诗学视作文化心智模仿的本土语法构型,解析其诗论模式和范畴基础等构建问题,并从本体论诗学、诗性元范畴和本土化解读三个层面入手渐次展开相应的讨论。第一节分析了本体论的诗学这一基础命题,包括诗性本质的三个基本特征——神圣性、原始性和规范性,以及叙事艺术发展阶段的三种基本形态——原始史诗、成熟史诗和变异史诗。第二节剖析了诗性的元范畴论题,涵盖艺术化自然的关系论和宇宙结构论(三界、时空和数量)两组内容。第三节论析了本土化的解读问题,关涉形象的类型化(正反面人物及坐骑)和诗学的概念基础(意象、韵律、风格)两方面。第四节总结了文化心智模仿的诗学原则和语法构架特征,其以使用艺术哲学的诗学审美理论,并从宏观历时视角揭示口传史诗整体传统的民俗审美及其思维原型为立论点。
第五章作为结论,考察了史诗类型学和史诗诗学的批评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概括并总结了它们在本土视野下所构建的学理性经验与反思示范意义,以及社会行动·文化心智模仿的生成机制原理。第一节,以文本分析的类型批评作为一种类型学范式的归结点,分析了类型学批评的三个论域:以时空范畴的溯源方法为中心的发生论批评、以社会文化的历史原型为依据的还原论批评、以类型发展的分类学方法为主线的发展论批评。第二节,以文本解读的诗学批评作为一种诗学范式的汇集点,论析了诗学批评的三个视域:以思维特征和审美结构为中心的本体批评、以艺术史视野和关系结构论为基础的形态批评、以民族诗学的传统基石为核心的本土批评。第三节,侧重比较和未来展望,就史诗类型学和诗学研究在社会民俗理论与文化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及发展趋向做了展望。第四节,论证了民俗文化语法系统的社会理论基础问题,包括社会文化的系统根基、口传文化类型的理论视角等。在此,这项工作不再局限于近些年所谓的单一田野经验主义风格之束缚,而是通过从具体案例到理论构拟的解析视角,对其包括蒙古史诗在内的口传文化类型及其语法系统做了全面而详细的论证考察。
综上所述,本书所涉内容框架如下:引言和第一章所探讨的是以两位学者代表性著述中的基本思想和核心观点为基础的类型学、诗学两大课题和总体论述,包括三组六个问题的具体考察、学理思考和理论梳理。第二章理论方法的历史溯源侧重于基本问题的脉络追溯,从每个论题的基本概念及其思想和方法论来源入手,通过实例研究与概念性论题的比较分析,追溯其理论或方法论问题的思想承继关系与方法论渊源。第三章史诗类型学方法和第四章史诗诗学视域着眼具体观念问题的解读和分析,围绕核心概念和核心理念,结合各自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研究特色,评述每个理论和方法论的形成、发展与成形的基础性课题。第五章重在本土化的经验和反思等,专注于以评价和展望为中心的综合考察。换句话说,本书就是关于史诗类型学和诗学问题——有关社会行动·文化心智模仿的文化语法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性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解析路径:基本问题的历史追溯、具体问题的解读和分析,以及通过综合考察给出评价和展望。
[1]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以社会行动·文化心智+本体即模仿统合了其史诗与社会·文化对应的内在性。
[2] Social Dramatic Theory是指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社会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社会戏剧或拟剧”和人类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倡的“剧场国家”等社会文化理论之假设。
[3] G.Kluckhohn,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Brown Unirevsity Prees,1961.
[4] 关于史诗类型学,见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修订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94年初版);《蒙古英雄史诗源流》(简称《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关于史诗诗学,见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古文,简称《史诗的诗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
[6] [美]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珩等译,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7]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 [美]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美]理查德·鲍曼(R.Bauman):《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英]哈夫洛克:《希腊人的正义观——从荷马史诗的影子到柏拉图的要旨》,邹丽等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11] 本书是根据笔者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修改而来的;需要说明的是,借助“社会”系统(行动联合或组合)的史诗类型学(《〈江格尔〉论》《蒙古英雄史诗源流》)来揭示其所依赖的行动模仿这一语法根基,而通过“心智(或文化)” 系统(聚合结构)的史诗诗学(《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来表示其所遵循的心智·思维或性格模仿这一语法基础。即,用有关社会行动和文化心智的模仿——文化语法来阐释或理解史诗材料和史诗学理论两者的本体关联,进而确定了笔者对史诗类型学和史诗诗学的的总体把握和阐释框架。
[12] 社会,与英语的society对应,是指生活、习俗、经济、制度、仪式和宗教等行动方式的总和。因此,“社会”这一关键词(书名)也指兼具community和society意味的和重于礼俗传统的非法理团体,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和黑格尔(hegel)等提出有关史诗中常见模仿“英雄时代”的那种团体文化或社会。从社会行动组合看,行动或功能与英语的Action 或 function对应,常见的例子有韦伯(M.weber)的“行动”、普罗普(В.Я.Пропп)的“功能”等。
[13] 模仿,与英语的imitation对应;“模仿”这一关键词(书名),借助柏拉图——“模仿接近分有”、亚里士多德——“史诗即人物行动的整体模仿”和塔尔德(G.Tarde)——“社会模仿”三者的重叠性进行统合,凸显了其现象背后数理统计逻辑的客观存在性。在柏拉图的定义里,模仿指现实对理念的和艺术对现实的两层模拟或再现原则,即模仿接近分有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史诗或其他艺术形式里有两种模仿:对人物行动的模仿和对人物性格的模仿。塔尔德指出,普遍重复性规律包括波动、生成和模仿,与此对应的有物理振动、生物遗传和社会模仿。社会模仿,可分为优势者(逻辑)律、超逻辑律(先外后内)、几何级数增律。
[14] 作为文化(culture)的核心部分,心智(Mind或mentality)介乎于思维或思想和心态之间,与英语的Mind和mentality之间的含义对应。即“心智”这一关键词(书名),指文化即心智的性格结构,包括思维模式、性格或人格的结构。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与英语的culture对应,一般指产生意义的一切行为或心智模式;Mind和mentality的统合接近思维背后的逻辑或性格personality——用感受、观察、理解、判断进行的思维能力的总和。在学界,以mentality解说列维-布留尔(Lvy-Bruhl)的原始思维(primitive mentality),以Mind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The Savage Mind,与法语La Pensee Sauvage对应),而psychic unity of mankind则专门指心理一致说。
[15] 自然与英语的nature对应,这里泛指与物的世界关联的生境、情境、环境或背景等,可统称“构境”。
[16] 智识介于智慧和知识之间,与英语的Intelligence或knowledge之间的含义对应,通常指经由经验获得的和不经由经验直接获得的思维模式和认知状态。
[17] 书中,提倡社会文化人类学等综合视野下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度对话模式,试图跃出纯粹民俗学或民间文艺学视角(原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自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单一藩篱,并批判性地借鉴柏拉图式的逻辑学(形而上学,除对理念的宗教化理解外)、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有关史诗模仿英雄人物或英雄精神的学说和塔尔德关于优势者(逻辑)律、超逻辑律(先外后内)、几何级数增律的社会模仿律等相关理论范式,还通过有关史诗类型学和史诗诗学的理论实例和逻辑修正来进一步考证并探索了包括史诗等在内的口语文化传统背后的数理统计逻辑的基本法则和结构方程原理(主要体现在拙著引言和结论等部分)。
[18]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2页。
[19] [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 2020年版。另见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0] 需要注意的是,艺术发生的本质论主要有:再现说(representation theory)、表现说(expression theory)和反映说(resemblance theory)。根据相关解说,再现说或摹仿说,皆是艺术本质的发生学说,含有客观的objective或模仿的mimetic等意思,在这一点很接近。表现说强调主观精神的艺术性表达或表现,而反映说则主张艺术源自主观精神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21] [英]泰勒(E.Tylo):《原始文化 ——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2] 朝戈金:《口头诗学的文本观》,《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论口头文学的接受》,《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上述文章提出整序接受的视角,用来描述并说明这种口语文化的规律性现象。
[23] [日]佐藤洋子:『「文明」と 「文化」の変容 』、『早稲田大学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紀要 3』1991年版、第45—73页。
[24]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25]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12、320页。
[26]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331、334—335页。
[27]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8] 关于维柯(Vico)、卡西尔(E.Cassirer)等,详见阿拉德尔吐《生活世界的跃东与呈现——比较视野下的超文化诗学及民族志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29] 自博阿斯(F.Boas)的文化相对论以来,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及阐释主义、利奇和普理查德(E.Prichard)等有关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论、加芬克尔(H.Garfinkel)的常人或民俗学方法论等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相关领域及其后现代主义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0] [美]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13页。柏拉图学说式的“类型逻辑思维”,强调真理永恒的不变性和规律的唯一性;达尔文(Darwin)学说式的“总体逻辑思维”,强调变化是规律,注重个体和差异性。
[31] 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32] [日]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季红真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第一次性制度指与婴幼儿期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或习惯样式,作为人格形成的共通样式,这一“基本的人格结构”是个体一生中保持固定不变的最重要的人格基础。第二次性制度,是指各种各样的禁忌规则、宗教仪式、民间传说、思维方式等,也是被基本人格“投射”而创造出来的延伸部分,叫作“投射体系”。
[33] 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季红真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0、112—114、118页。
[34] [日]津城寛文:『日本の深層文化と宗教 』、國學院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第129—130页。
[35] [日]祖父江孝男:『文化とパーソナリティ 』,弘文堂1976年版。根据《简明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的中译本)的第四章即核心部分,另见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季红真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7页。
[36] 对结构(法则)和功能(机制)的区分,法则(物理学定律)意味标准的公式化和方程化,机制(生物学的功能获经济学的价格)说明相对灵活的动态或波动规律。另见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2期;根据埃尔斯特(Elster)的看法:如果条件为C1,C2,…Cn,E总是成立,那么E即法则,如果条件为C1,C2,…Cn,E有时成立,那么E即机制。
[37] [美]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38] 知识或智识哲学,是指基于无文字社会类型的口语·非遗文化研究及其人文主义的总称。无论是博阿斯、列维-布留尔等的“原始”或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等表述,还是沃尔特·翁从“原始”或“无文字”到“口语”等负载着差异的沉重字眼——“低等”(inferior),均考虑到了这类术语所隐含着的偏见和不平等性。另见[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39]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0] 朱元发:《涂尔干社会学引论》,远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41] [法]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49页。此外,塔尔德推出《社会逻辑》(1895)一书并解释说,基本现象在无穷无尽的重复中结合成为具体的群体、团体、体系等,尤其是精神体系和社会体系。这个过程是一种逻辑、综合,是不断重复的过程。这是一个包含适应、发明和组织的过程。
[42] [法]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6页。书中认为,重复性的普遍规律包括波动、生成和模仿,与此对应的有物理振动、生物遗传和社会模仿,其中社会模仿又可分为三个方面。1.几何级数增律:在无干扰的统计学假设下,模仿行动一旦开始,传播速度以几何级数增长;2.优势者或逻辑律:在“思想在先,模仿在后”的逻辑前提下,形成按照风俗或时尚的仪式和程序进行的模仿,包括向优势者模仿,权威和说服的转化倾向等下降律;3.超逻辑律,即从内心到外表的模仿,一般指轻信(credibility)与顺从(obedience)等逻辑不起作用的形式,也就属于信念(belief)和欲望(desire)模仿,也包括个体对本土以外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与选择,总是优先向外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先外后内)模仿。
[43] 详见 [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含《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神话学——裸人》),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4] 关于史密斯(R.Smiths)、弗雷泽(Frazer)、涂尔干、莫斯(Marcel Mauss)等的观点,详见[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汪培基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法]毛斯(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神话仪式学派和社会形态学等提出,神话等故事叙述源于对仪式活动、禁忌习俗的解释,深层意识基础是有关自然循环和四季更替等的行动模仿。
[45] 详见[加]弗莱(Northrop Frye)《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185—277页。
[46] 关于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lnnis)、麦克卢汉(M.McLuhan)、瓦尔特·翁(W.J.Ong)等,详见[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英文初版1964年),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加]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杨晨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
[47] 详见[英]亚瑟·布雷德利(Arthur Bradley)《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主义,包括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观和语音中心主义两个方面。在他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因此,它是“以现实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
[48] 详见阿拉德尔吐《生活世界的跃东与呈现——比较视野下的超文化诗学及民族志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109、113—115、119—121、122—124、125—127页。
[49] [苏]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1—95页。
[50] [美]卢因(Kurt Lewin):《社会科学中的场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场论公式为B=f(P,E)=f(LSP),即行为(B)依赖于人(P)和环境(E)的相互作用。与此相同,在《文化的进化》(1959)中,怀特(L.A.White)提出有关人类学的新进化思想,认为文化作为一个超有机体,也就说,文化的进步就等于“每人每年利用能量总量之增长”或“利用能量的技术效率之提高”。因此,文化的发展或进化所遵循的公式为:C=ET,其中C表示文化(culture)或进化状态,E指人均年利用的能量(energy),T则指能源开发的工具和效率,即技术(technology)。
[51]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52] 构建主义,有时以接近理性主义或现代科学主义等名称及含义出现;阐释主义,也有诠释或解释主义等不同称谓法;等等。例如,James Mahoney提倡集合论分析(set-theoretic analysis)的科学建构主义(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着重讨论社会科学认识论中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科学方法和建构主义方法的关系论题,进而对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偏见表现出了批判的态度。见James Mahoney,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1;Gregory Wawro,Ira Katznelson,Time Counts: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
[53] [美]米伯克(Michael s.Lewi-Bck)、布里曼(Alan Bryman)、廖福挺(Tim Futing Liao)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第2卷),沈崇麟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0—724页。
[54] 对回归分析的线性代数基础和矩阵模式探讨;详见[美]谢宇《回归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美]A.班纳(Adrian Banner)《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修订版),杨爽、赵晓婷、高璞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
[55]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88页;另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一般认为,数学基础研究也包括直觉主义、形式主义和逻辑主义等。
[56] [美]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91页。
[57] [美]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87页。
[58] 巴·布林贝赫:《蒙古族诗歌美学论纲》(蒙古文,简称《论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